使用者:A15928872517/"History of macroeconomic thought"
宏觀經濟思想史
[編輯]來自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宏觀經濟學理論起源於商業周期和貨幣理論的研究。[1][2]一般來說,早期的理論家認為貨幣因素不能影響實際產出等實際因素。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攻擊了一些這些"經典"理論,並提出了一種通用理論,該理論將整個經濟描述為總體而非單獨的微觀經濟部分。 他試圖解釋失業和經濟衰退,注意到在經濟衰退期間,人們和企業傾向於囤積現金並避免投資。 他辯稱,這否定了古典經濟學家的假設,即市場總是清澈的,不會留下商品過剩和願意勞動力的閒置。[3]
跟隨凱恩斯的一代經濟學家將他的理論與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相結合,形成了新古典主義的綜合。 儘管凱恩斯理論最初省略了對價格水平和通貨膨脹的解釋,但後來的凱恩斯主義者採用了菲利普斯曲線來模擬價格水平的變化。 一些凱恩斯主義者反對將凱恩斯的理論與均衡系統結合的綜合方法,而是提倡非均衡模型。 以米爾頓·佛利民為首的貨幣主義者採納了一些凱恩斯主義的觀點,比如對貨幣需求的重要性,但認為凱恩斯主義者忽視了貨幣供應在通貨膨脹中的作用。[4]羅伯特·盧卡斯和其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批評了在理性預期下行不通的凱恩斯模型。 盧卡斯還辯稱,凱恩斯的經驗模型不會像基於微觀經濟基礎的模型那樣穩定。
新的古典學派最終形成了真實的商業周期理論。 像早期的經典經濟模型一樣,皇家銀行模型假設市場已經明朗,並且商業周期是由技術和供應的變化驅動的,而不是需求。 新凱恩斯主義者試圖解決盧卡斯和其他新古典經濟學家對新凱恩斯主義者提出的許多批評。 新凱恩斯主義者採納了理性的預期,並建立了以粘性價格為微觀基礎的模型,這表明經濟衰退仍然可以由需求因素解釋,因為剛性阻止了價格降至市場清盤水平,從而留下了商品和勞動力的過剩。 新的新古典主義綜合理論將新古典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元素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共識。 其他經濟學家迴避了關於短期動態的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辯論,發展了新的長期經濟增長理論。[5]大衰退導致了該領域的現狀回顧,一些公眾的關注點轉向了異端經濟學。
起源
[編輯]
宏觀經濟學源自兩個研究領域:商業周期理論和貨幣理論。貨幣理論可以追溯到16世紀,由馬丁·德·阿斯皮爾庫埃塔提出,而商業周期分析則始於19世紀中葉。
商業周期理論
[編輯]從19世紀60年代的威廉·斯坦利·傑文斯和克萊門特·朱格拉開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釋經濟活動頻繁且劇烈變化的周期。[9] 這一努力的一個關鍵里程碑是韋斯利·米切爾於1920年創立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這標誌著經濟波動理論統計模型(基於周期和趨勢而非經濟理論的模型)的繁榮的開始,這些模型導致了像庫茲涅茨浪潮這樣的看似規律的經濟模式的發現。[10]
其他經濟學家在他們的商業周期分析中更側重於理論。 大多數商業周期理論都集中在單一因素上,比如貨幣政策或天氣對當時主要農業經濟的影響。[8] 儘管商業周期理論在20世紀20年代已經相當成熟,但丹尼斯·羅伯遜和拉爾夫·霍特里等理論家的工作對公共政策影響甚微。他們的部分均衡理論無法捕捉到市場相互作用的普遍均衡;特別是早期的商業周期理論將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分開處理。[9] 這些領域的研究使用微觀經濟方法來解釋就業、價格水平和利率。[12]
貨幣理論
[編輯]最初,價格水平與產出之間的關係是由貨幣的數量理論解釋的;大衛·休謨在他的1752年著作《貨幣論》(論文集,道德、政治和文學,第二部分,第三篇)中提出了這一理論。數量理論通過薩伊定律來審視整個經濟,該定律指出,供應給市場的商品將會被出售——簡而言之,市場總是清倉的。[3] 在這種觀點下,貨幣是中立的,不能影響經濟中的實際因素,如產出水平。 這與經典的二元觀點一致,即經濟的實際方面和名義因素,如價格水平和貨幣供應量,可以被認為是相互獨立的。例如,向經濟中添加更多資金只會提高價格,而不是創造更多的商品。[15]
貨幣的數量理論主導了宏觀經濟理論,直到20世紀30年代。 兩個版本特別有影響力,一個是由歐文·費雪在1911年出版的《貨幣的購買力》等作品中發展起來的,另一個則由劍橋經濟學家在20世紀初提出。費舍爾的數量理論可以通過保持貨幣流通速度(給定貨幣在交易中使用頻率)和實際收入(質量)不變,並允許貨幣供應量(質量)和價格水平(質量)在交換方程中變化來表達:[16]
大多數古典理論,包括費舍爾的理論,都認為速度是穩定的,並且獨立於經濟活動。劍橋經濟學家,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開始挑戰這一假設。 他們提出了劍橋現金平衡理論,該理論研究了貨幣需求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劍橋理論並不假設貨幣的需求和供給總是處於平衡狀態,它解釋了當經濟下滑時人們持有更多現金的情況。 通過考慮持有現金的價值,劍橋經濟學家朝著凱恩斯後來發展的流動性偏好概念邁出了重要一步。劍橋理論認為人們持有貨幣有兩個原因:促進交易和維持流動性。 在後來的研究中,凱恩斯在他的流動性偏好理論中添加了第三個動機——投機,並在此基礎上創建了他的通用理論。[19]
1898年,努特·維克塞爾提出了一種以利率為中心的貨幣理論。 他的分析使用了兩種利率:由銀行系統確定的市場利率和由資本回報率確定的實際或"自然"利率。在威克塞爾的理論中,當技術創新導致自然利率上升或銀行系統允許市場利率下降時,累積通脹就會發生。 累積通縮發生在相反的情況下,導致市場利率升至自然水平以上。[2] 威克塞爾的理論並沒有產生貨幣數量與價格水平之間的直接關係。 根據威克塞爾的觀點,只要自然貨幣超過市場利率,貨幣就會在內生中被創造出來,而硬通貨的數量不會增加。 在這種情況下,借款人將利潤轉化為現金存入銀行儲備,從而擴大貨幣供應量。 這可能導致一個累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脹持續上升而貨幣基礎沒有擴大。 威克爾的工作影響了凱恩斯和斯德哥爾摩學派中的瑞典經濟學家。[21]
凱恩斯通論
[編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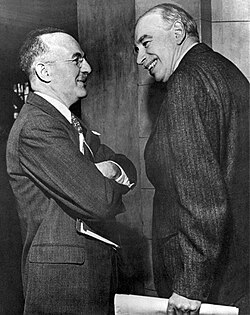
現代宏觀經濟學可以說始於凱恩斯,並於193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擴展了流動性偏好的概念,並建立了一個關於經濟運作的一般理論。 凱恩斯的理論首次將貨幣因素和實際經濟因素結合起來,[9] 解釋了失業問題,並提出了實現經濟穩定的政策建議。[23]
凱恩斯認為經濟產出與貨幣流通速度呈正相關。他通過改變流動性偏好來解釋這種關係:人們在經濟困難時期通過減少支出來增加資金持有量,這進一步放緩了經濟增長。 這個節儉的悖論聲稱,個人在經濟衰退中生存的努力只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當對貨幣的需求增加時,貨幣流通速度就會減慢。 經濟活動放緩意味著市場可能無法清理,導致過剩商品浪費和產能閒置。凱恩斯顛覆了數量理論,認為市場變化會改變數量而不是價格。凱恩斯用固定價格水平的假設取代了穩定速度的假設。 如果支出減少而價格沒有下降,商品的過剩會減少對工人的需求並增加失業率。[28]
古典經濟學家難以解釋非自願失業和經濟衰退,因為他們將薩伊定律應用於勞動力市場,並期望所有願意以現行工資工作的人都能就業。在凱恩斯的模型中,就業和產出由總需求驅動,即消費和投資的總和。 由於消費保持穩定,總體需求的大多數波動都源於投資,而投資是由許多因素驅動的,包括預期、"動物精神"和利率。凱恩斯認為財政政策可以補償這種波動。 在經濟衰退期間,政府可以增加支出以購買過剩商品並雇用閒置勞動力。此外,乘數效應增加了這種直接支出的效果,因為新雇用的工人會花費他們的收入,這些收入會滲透到整個經濟中,而企業則會投資以應對需求的增長。[25]
凱恩斯關於強烈公共投資的建議與他對不確定性的興趣有關。凱恩斯在1921年出版的《概率論》一書中提供了對統計推斷的獨特視角,這比他的主要經濟著作早了很多年。凱恩斯認為,強大的公共投資和財政政策可以抵消經濟波動不確定性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 雖然凱恩斯的繼任者很少關注他工作中的概率部分,不確定性可能在一般理論的投資和流動性偏好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32]
凱恩斯工作的確切含義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爭議。 甚至凱恩斯關於失業的政策建議的解釋,作為一般理論中較為明確的一部分,也成為了辯論的主題。 經濟學家和學者們爭論凱恩斯的建議是旨在通過重大政策轉變來解決一個嚴重的問題,還是通過適度保守的解決方案來處理一個小問題。[34]
凱恩斯的繼任者
[編輯]凱恩斯的繼任者們討論了凱恩斯模型的確切表述、機制及其後果。 一組代表了凱恩斯的"正統"解釋; 他們將古典微觀經濟學與凱恩斯思想相結合,產生了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初主導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凱恩斯主義者的兩個陣營對這種對凱恩斯的綜合解釋提出了批評。 一組關注凱恩斯作品中的不平衡方面,而另一組則對凱恩斯持原教旨主義立場,並開始了後凱恩斯主義的異端傳統。[37]
新古典綜合理論
[編輯]主條目: 新古典綜合
跟隨凱恩斯的一代經濟學家,即新凱恩斯主義者,通過將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相結合,創造了"新古典綜合"。新凱恩斯主義者處理了兩個微觀經濟問題:首先,為凱恩斯理論的某些方面,如消費和投資奠定基礎;其次,將凱恩斯宏觀經濟學與一般均衡理論相結合。[39] (在一般均衡理論中,各個市場相互作用,如果存在完全競爭、沒有外部性和完美信息,則存在均衡價格。)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1947年)為這一綜合提供了大量的微觀經濟基礎。薩繆爾森的工作為新凱恩斯主義者使用的方法論樹立了典範:用正式的數學模型表達的經濟理論。儘管凱恩斯的理論在這一時期占主導地位,他的繼任者們大多放棄了他非正式的方法論,轉而支持薩繆爾森的理論。[42]
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已經停止了對凱恩斯主義的辯論,接受了綜合觀點;然而,仍然存在分歧的空間。綜合分析將市場清理的問題歸因於粘性價格,這些價格未能調整以適應供需的變化。另一組凱恩斯主義者專注於非均衡經濟學,並試圖在缺乏市場清算的情況下調和均衡的概念。[46]
新凱恩斯模型
[編輯]主條目: 新凱恩斯經濟學

1937年,約翰·希克斯[a]發表了一篇文章,將凱恩斯的思想納入了一個總體均衡框架中,在這個框架下,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整體均衡中相遇。希克的"投資-儲蓄/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模型成為了20世紀60年代數十年理論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基礎。該模型用信息安全曲線表示商品市場,該曲線是一組代表投資和儲蓄均衡的點。 貨幣市場均衡用貨幣模型曲線表示,該曲線是一組代表貨幣供需平衡的點。 曲線的交集識別了經濟中的總體均衡[50],其中利率和經濟產出具有唯一的均衡值。印度盧比模型側重於將利率作為"貨幣傳導機制",即貨幣供應影響總需求和就業等實際變量的渠道。 貨幣供應量的減少會導致利率上升,從而減少投資並降低整個經濟的產出。其他經濟學家則基於信息系統/生命周期管理框架進行構建。 值得注意的是,1944年,法蘭科·莫迪利安尼[b]增加了勞動力市場。 莫迪利亞尼的模型將經濟描繪成一個在勞動、金融和商品等相互關聯的市場中普遍均衡的系統,並用嚴格的名義工資來解釋失業問題。[53]
增長曾引起亞當·斯密等18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興趣,但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邊緣主義革命期間,當研究人員專注於微觀經濟學時,研究工作逐漸減少。當新凱恩斯主義者羅伊·哈羅德和埃弗塞·多馬獨立發展哈羅德-多馬模型時,經濟增長的研究重新興起。哈羅德-多馬爾模型是將凱恩斯的理論擴展到長期領域,而凱恩斯自己對此也沒有進行過研究。他們的模型結合了凱恩斯的乘數效應和投資加速器模型,得出了一個簡單的結果:增長率等於儲蓄率除以資本產出比率(資本總額除以產出總額)。哈羅德-多馬爾模型主導了增長理論,直到1956年羅伯特·索洛[c]和特雷弗·斯旺[d]獨立開發了新古典增長模型。索洛和斯旺提出了一種更具經驗吸引力的模型,該模型基於生產中勞動力和資本的替代,實現了"平衡增長"。索洛和斯旺建議,增加儲蓄只能暫時促進經濟增長,而只有技術改進才能在長期內增加增長。在索洛和斯旺之後,從1970年到1985年,增長研究逐漸減少,幾乎沒有任何關於增長的研究。[55]
經濟學家將綜合理論工作融入到大規模的宏觀計量經濟模型中,該模型結合了消費、投資和貨幣需求等因素的個別方程與經驗觀測數據。這項研究在莫迪利亞尼及其合作者開發的麻省理工學院-賓大-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模型下達到了頂峰。[61] 宏觀經濟學結合了信息素養與其他方面的綜合分析,包括新古典增長模型和通脹與產出之間的菲利普斯曲線關係。大型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都成為了綜合理論批評者的目標。
菲利普斯曲線
[編輯]主條目: 菲利普斯曲線

凱恩斯並沒有明確闡述價格水平的理論。早期的凱恩斯模型假設工資和其他價格水平是固定的。這些假設在20世紀50年代通脹穩定時並未引起太多關注,但到了60年代中期,通脹率上升,並成為宏觀經濟模型的問題。1958年,威廉·菲利普斯[e]提出了一個價格水平理論的基礎,他實證觀察到通貨膨脹和失業似乎呈反比關係。 1960年,理察·利普西{{efn|Lipsey, R.G.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2–1957: A Further Analysis. Economica. February 1960, 27 (105): 1–31. JSTOR 2551424. doi:10.2307/2551424.首次提供了這一相關性的理論解釋。 一般來說,凱恩斯主義對曲線的解釋認為,過剩的需求推動了高通脹和低失業率,而產出缺口則提高了失業率並抑制了物價。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菲利普斯曲線面臨著實證和理論方面的攻擊。 曲線所代表的產出與通脹之間的假設權衡是凱恩斯體系中最薄弱的部分。[69]
失衡的宏觀經濟學
主條目: 失衡的宏觀經濟學
儘管新古典主義綜合理論盛行,但它也有凱恩斯主義的批評者。 一種不平衡或"非瓦爾拉斯"理論被提出[70],該理論批評這種綜合理論在允許不平衡現象,特別是非自願失業,在平衡模型中建模時存在明顯的矛盾。此外,他們認為,一個市場的失衡必須與另一個市場的失衡相關聯,因此非自願失業必須與商品市場的過剩供應掛鉤。 許多人認為唐·帕廷金的作品是失衡領域中的第一部。羅伯特·克洛爾(1965)[f]提出了他的"雙重決策假說",即市場中的人可能決定自己想買什麼,但最終他的購買量取決於他能賣出多少。克洛爾和阿克塞爾·萊昂胡夫德(1968)[g]認為,不平衡是凱恩斯理論的基本部分,值得更多的關注。羅伯特·巴羅和赫歇爾·格羅斯曼提出了普遍的非均衡模型[h],在這些模型中,個別市場在形成普遍均衡之前就已經鎖定在價格中。 這些市場產生了"虛假價格",導致了失衡。巴羅和格羅斯曼的工作不久後,不平衡模型在美國失寵了,巴羅放棄了凱恩斯主義,採納了新的經典市場清算假設。[78]凱恩斯並沒有明確闡述價格水平的理論。早期的凱恩斯模型假設工資和其他價格水平是固定的。這些假設在20世紀50年代通脹穩定時並未引起太多關注,但到了60年代中期,通脹率上升,並成為宏觀經濟模型的問題。1958年,菲利普斯提出了一個價格水平理論的基礎,他實證觀察到通貨膨脹和失業似乎呈反比關係。 1960年,理察·利普西首次提供了這一相關性的理論解釋。 一般來說,凱恩斯主義對曲線的解釋認為,過剩的需求推動了高通脹和低失業率,而產出缺口則提高了失業率並抑制了物價。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菲利普斯曲線面臨著實證和理論方面的攻擊。 曲線所代表的產出與通脹之間的假設權衡是凱恩斯體系中最薄弱的部分。[69]
失衡的宏觀經濟學
[編輯]主條目: 失衡的宏觀經濟學 儘管新古典主義綜合理論盛行,但它也有凱恩斯主義的批評者。 一種不平衡或"非瓦爾拉斯"理論被提出[70],該理論批評這種綜合理論在允許不平衡現象,特別是非自願失業,在平衡模型中建模時存在明顯的矛盾。此外,他們認為,一個市場的失衡必須與另一個市場的失衡相關聯,因此非自願失業必須與商品市場的過剩供應掛鉤。 許多人認為唐·帕廷金的作品是失衡領域中的第一部。羅伯特·克洛爾(1965)提出了他的"雙重決策假說",即市場中的人可能決定自己想買什麼,但最終他的購買量取決於他能賣出多少。克洛爾和阿克塞爾·萊昂胡夫德(1968)[i]認為,不平衡是凱恩斯理論的基本部分,值得更多的關注。羅伯特·巴羅和赫歇爾·格羅斯曼提出了普遍的非均衡模型,在這些模型中,個別市場在形成普遍均衡之前就已經鎖定在價格中。 這些市場產生了"虛假價格",導致了失衡。巴羅和格羅斯曼的工作不久後,不平衡模型在美國失寵了,巴羅放棄了凱恩斯主義,採納了新的經典市場清算假設。[78]

雖然美國經濟學家很快放棄了非均衡模型,歐洲經濟學家則更願意接受沒有市場清算的模型。像埃德蒙·馬林瓦德和雅克·德雷茲這樣的歐洲人擴展了不平衡的傳統,並努力解釋價格剛性,而不是簡單地假設它。馬林沃德(1977)[j] 利用不平衡分析發展了一種失業理論。他辯稱,勞動和商品市場的失衡可能導致商品和勞動力的配給,從而引發失業。馬林瓦德採納了固定價格框架,並認為與主導農業經濟的相對靈活的原材料定價系統相比,現代工業價格的定價將較為僵化。[82] 價格固定,僅限數量調整。馬林沃德認為,在古典和凱恩斯失業的情況下,達到均衡狀態的可能性最大。[83] 新古典主義傳統中的工作被限制為馬林沃德類型學的一個特例,即瓦爾拉斯均衡。 在馬林沃的理論中,由於工業定價的性質,幾乎不可能達到瓦爾拉斯均衡情況。[83]
貨幣主義
[編輯]主條目: 貨幣主義
米爾頓·佛利民提出了一種替代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方法,最終被標記為貨幣主義。 一般來說,貨幣主義認為貨幣供應對宏觀經濟很重要。當貨幣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出現時,凱恩斯主義者忽視了金錢在通貨膨脹和商業周期中的作用,而貨幣主義直接挑戰了這些觀點。[4]
批評和增強菲利普斯曲線
[編輯]菲利普斯曲線似乎反映了通貨膨脹與產出之間明顯的逆向關係。 20世紀70年代,隨著經濟同時陷入停滯和被稱為滯脹的通貨膨脹,曲線崩潰了。 菲利普斯曲線的經驗性崩潰緊隨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費爾普斯基於理論發起的攻擊之後。 儘管菲爾普斯不是貨幣主義者,但他認為只有意外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才會影響就業。 菲爾普斯的"期望增強菲利普斯曲線"的各種變體成為了標準工具。 弗里德曼和菲爾普斯使用了沒有長期通脹和失業之間權衡的模型。 他們使用了基於自然失業率的模型,而不是菲利普斯曲線,在這種模型中,擴張性貨幣政策只能暫時將失業率降至自然失業率以下。 最終,企業會根據實際因素調整其價格和工資以應對通貨膨脹,忽略貨幣政策的名義變化。 擴張性的推動將被抹去。[85]
金錢的重要性
[編輯]安娜·施瓦茨與弗里德曼合作,創作了貨幣主義的重要作品之一《美國貨幣史》(1963年),該作品將貨幣供應與商業周期聯繫起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者基於大蕭條期間利率極低但產出仍然低迷的證據,採納了貨幣政策不會影響總產出或商業周期的觀點。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認為,凱恩斯主義者只關注名義利率,而忽視了通貨膨脹在大蕭條期間一直較高的實際利率中所起的作用。 實際上,貨幣政策實際上是緊縮的,對產出和就業施加了下行壓力,儘管經濟學家僅從名義利率來看認為貨幣政策具有刺激性。[88]
弗里德曼發展了自己的貨幣數量理論,該理論參考了歐文·費雪的理論,但繼承了凱恩斯的許多觀點。弗里德曼1956年的《貨幣數量理論:重述》[k] 將凱恩斯對貨幣的需求和流動性偏好納入了一個類似於經典交換方程的方程中。弗里德曼更新的數量理論也允許使用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來解決重大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弗里德曼與凱恩斯決裂,他認為即使在經濟衰退期間,貨幣需求也相對穩定。貨幣主義者認為,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微調"是適得其反的。 他們發現,即使在財政政策調整期間,貨幣需求也保持穩定,[92] 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存在滯後現象,這使得它們過於緩慢,無法防止輕微的經濟下滑。[93]
突出與衰落
[編輯]
貨幣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吸引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弗里德曼和菲爾普斯版本的菲利普斯曲線在滯脹期間表現更好,增強了貨幣主義的可信度。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貨幣主義已成為宏觀經濟學中的新正統觀念,到了70年代末,英國和美國的中央銀行在制定政策時大多採納了以貨幣供應為目標而非利率的貨幣主義政策。然而,由於測量難度,中央銀行很難瞄準貨幣總量。[98] 1979年保羅·沃克接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時,貨幣主義面臨著重大考驗。 沃爾克收緊了貨幣供應量,降低了通貨膨脹,從而導致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降低了貨幣主義的受歡迎程度,但清楚地展示了貨幣供應在經濟中的重要性。[4] 當曾經穩定的貨幣流通速度與貨幣主義的預測相悖,並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美國出現波動時,貨幣主義的可信度降低了。[94] 貨幣主義的單等式模型和繪圖數據非統計分析方法也輸給了凱恩斯主義者青睞的同時等式建模。[99] 貨幣主義的政策和分析方法在中央銀行家和學者中失去了影響力,但其核心原則是貨幣的長期中立性(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不會對實際變量產生長期影響)以及使用貨幣政策來穩定宏觀經濟,甚至在凱恩斯主義者中也成為了宏觀經濟主流的一部分。[4][98]
新古典經濟學
[編輯]主條目: 新古典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從貨幣主義演變而來,並對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其他挑戰。 早期的新古典主義者認為自己是貨幣主義者,[101] 但新古典學派逐漸發展起來。 新古典主義者放棄了貨幣政策能夠系統性影響經濟的貨幣主義信念,[102] 最終採納了完全忽略貨幣因素的真實商業周期模型。[103]
新古典主義完全打破了凱恩斯經濟理論,而貨幣主義者則建立在凱恩斯主義思想之上。儘管拋棄了凱恩斯理論,新古典經濟學家還是分享了凱恩斯主義對解釋短期波動的關注。 新古典主義取代貨幣主義者成為凱恩斯主義的主要對手,並將宏觀經濟學的主要辯論從是否關注短期波動轉變為宏觀經濟模型是否應基於微觀經濟理論。像貨幣主義一樣,新古典經濟學也根植於芝加哥大學,主要是由小羅伯特·盧卡斯創立的。 新古典經濟學發展的其他領軍人物包括明尼蘇達大學的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和羅切斯特大學的羅伯特·巴羅。[103]
新古典經濟學家寫道,早期的宏觀經濟理論僅勉強基於微觀經濟理論,並將其努力描述為為宏觀經濟學提供了"微觀經濟基礎"。 新古典主義者也引入了理性預期,並認為鑑於經濟主體的理性預期,政府幾乎沒有能力穩定經濟。 最具爭議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重新提出了市場清算的假設,他們既假設價格具有靈活性,也認為市場應該以均衡狀態進行建模。[106]
理性預期與政策無關性
[編輯]
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認識到,人們的經濟決策基於對未來的預期。 然而,直到20世紀70年代,大多數模型都依賴於自適應預期,這種預期基於過去趨勢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在一段時間內通脹率平均為4%,經濟主體被假設預期第二年的通脹率為4%。1972年,[l]在約翰·穆斯[m]1961年的一篇農業經濟學論文的影響下,盧卡斯將理性預期引入了宏觀經濟學。本質上,適應性預期將行為建模為回顧性,而理性預期則建模為前瞻性的經濟主體(消費者、生產者和投資者)。新古典經濟學家還聲稱,如果一個經濟模型假設其所建模的代理行為好像他們不知道該模型的存在,那麼該模型在內部將是不一致的。在理性預期的假設下,模型假設代理基於模型本身的最優預測進行預測。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具有完美的遠見,而是他們基於對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深入理解行事。[114]
湯瑪斯·薩金特和尼爾·華萊士(1975)[n]將理性預期應用於菲利普斯曲線中通脹與產出之間的模型,發現貨幣政策無法系統地穩定經濟。 薩金特和華萊士的政策無效性命題發現,經濟主體會在貨幣刺激措施增加就業和產出之前,預測通貨膨脹並調整到更高的價格水平。只有未預期的貨幣政策才能增加就業,而且沒有任何中央銀行能夠在沒有經濟主體在價格變化產生刺激性影響之前,系統地利用貨幣政策進行擴張。[116]
羅伯特·埃。[o] 霍爾將理性預期應用於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說,即人們當前的消費水平基於他們的財富和終身收入,而不是當前收入。霍爾發現,人們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平滑他們的消費,並且只有在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發生變化時才會改變消費模式。霍爾和弗里德曼關於永久收入假說的版本都挑戰了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即像減稅這樣的短期穩定政策可以刺激經濟。永久收入觀點認為消費者應以財富為基礎進行消費,因此收入的暫時增長只會產生適度的消費增加。經驗測試表明,霍爾假設可能低估了由於收入增加而導致的消費增長;然而,霍爾的工作幫助普及了歐拉消費方程模型。[119]
盧卡斯批判與微觀基礎
[編輯]1976年,盧卡斯撰寫了一篇論文[p],批評用於預測和政策評估的大規模凱恩斯模型。 盧卡斯認為,基於變量之間經驗關係的經濟模型在政策變化時是不穩定的:在一個政策制度下,關係可能在制度變化後失效。盧卡斯的批評更進一步,認為政策的影響取決於該政策如何改變經濟主體的預期。 沒有模型是穩定的,除非它考慮了預期以及預期如何與政策相關。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放棄凱恩斯主義的不均衡模型,專注於基於結構和行為的均衡模型可以糾正這些缺陷。凱恩斯經濟學家通過建立基於穩定理論關係的微觀基礎模型作出了回應。[122]
盧卡斯供給理論和商業周期模型
[編輯]參見: 盧卡斯群島模型
盧卡斯和倫納德·雷平[q]在1969年首次提出了新的古典總量供給方法。 在他們的模型中,就業的變化基於工人對閒暇時間的偏好。 盧卡斯和雷平將就業減少建模為工人自願選擇減少工作努力,以應對當前的工資水平。[123]
盧卡斯(1973)[r] 提出了一種基於理性預期、不完美信息和市場清算的商業周期理論。 在構建這個模型時,盧卡斯試圖納入一個經驗事實,即通貨膨脹和產出之間存在權衡,同時不妥協貨幣在短期內是非中性的。這個模型包含了貨幣驚喜的概念:貨幣政策只有在人們因商品價格相對變化而感到驚訝或困惑時才重要。盧卡斯假設生產者會在認識到其他行業的變化之前,就已經意識到自己行業的變化。 基於這一假設,生產者可能會將整體價格水平的提高視為對其商品需求的增加。 生產商通過增加產量來回應,卻發現整個經濟中的價格普遍上漲,而不是專門針對他的商品。這個"盧卡斯供給曲線"模型的輸出取決於"價格"或"貨幣驚喜",即預期通脹與實際通脹之間的差異。盧卡斯的"驚喜"商業周期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後失寵,因為實證證據未能支持這一模型。[127][128]
實際商業周期理論
[編輯]
儘管"金錢驚喜"模式受挫,但仍繼續努力開發一個新的經典商業周期模型。 1982年,基德蘭和普雷斯科特[s]發表的一篇論文介紹了真實商業周期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商業周期完全可以由供給側來解釋,模型表示的是系統處於恆定平衡狀態的經濟。皇家銀行忽視了用價格驚喜、市場失靈、價格粘性、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來解釋商業周期的必要性。相反,基德蘭和普雷斯科特構建了簡潔的模型,這些模型通過技術和生產力的變化來解釋商業周期。就業水平發生了變化,因為這些技術和生產力的變化改變了人們的就業欲望。皇家銀行拒絕了經濟衰退期間高非自願失業率的想法,不僅否定了金錢能夠穩定經濟的觀點,也否定了貨幣主義認為金錢可以破壞經濟穩定的觀點。[132]
真正的商業周期建模者尋求基於箭頭-德布羅一般均衡的微觀基礎來構建宏觀經濟模型。紅血球模型是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靈感來源之一。 分布式帳本技術模型已成為宏觀經濟學家常用的方法論工具,即使是那些不同意新古典理論的人也是如此。[129]
新凱恩斯經濟學
[編輯]主條目: 新凱恩斯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指出了新古典綜合理論內在的矛盾: 瓦爾拉斯微觀經濟學中的市場清算和一般均衡理論不能導致凱恩斯宏觀經濟學中市場未能清算的情況。 新凱恩斯主義者意識到了這一悖論,但新古典主義者放棄了凱恩斯,而新凱恩斯主義者則放棄了瓦爾拉斯和市場清理。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新凱恩斯研究人員調查了市場不完善(如壟斷競爭)、名義摩擦(如粘性價格)以及其他摩擦如何使微觀經濟學與凱恩斯宏觀經濟學保持一致。新凱恩斯主義者經常制定具有理性預期的模型,這些模型由盧卡斯提出,並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採納。[139]
名義剛度和實際剛性
[編輯]斯坦利·費希爾(1977)[t] 回應了湯瑪斯·薩金特和尼爾·華萊士的貨幣無效性命題,並展示了貨幣政策如何即使在具有理性預期的模型中也能穩定經濟。費舍爾的模型展示了在長期名義工資合同模型中,貨幣政策如何產生影響。[140] 約翰·B·泰勒進一步闡述了費希爾的研究,發現貨幣政策可能產生長期影響——即使在工資和價格調整之後也是如此。 泰勒通過基於費舍爾的模型,假設合同談判是分階段進行的,並且合同在較長時期內固定名義價格和工資率,得出了這一結果。這些早期的新凱恩斯理論基於這樣一個基本理念:給定固定的名義工資,貨幣當局(中央銀行)可以控制就業率。由於工資固定在名義利率上,貨幣當局可以通過改變貨幣供應量來控制實際工資(經通脹調整後的工資價值),從而影響就業率。[141]
到20世紀80年代,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這些早期的名義工資合同模型感到不滿,因為他們預測實際工資將是逆周期的(當經濟下滑時,實際工資會上升),而實證證據顯示實際工資往往獨立於經濟周期甚至略微順周期。這些合同模式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也沒有意義,因為不清楚企業為何會在長期合同導致低效率的情況下使用它們。新凱恩斯主義者沒有尋找勞動力市場的剛性,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商品市場以及由"菜單成本"價格變化模型導致的粘性價格。該術語指的是餐廳在想要更改價格時列印新菜單的實際成本;然而,經濟學家也用它來指代與更改價格相關的更一般的費用,包括評估是否進行更改的費用。由於企業必須花錢來改變價格,他們並不總是將價格調整到市場完全清空的地步,這種缺乏價格調整的情況可以解釋為什麼經濟可能處於失衡狀態。使用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數據的研究證實,價格確實傾向於具有粘性。 商品的價格通常每四到六個月變化一次,如果不包括銷售額,則每八到十一個月變化一次。[145]
雖然一些研究表明菜單成本太小,無法產生很大的總體影響,勞倫斯·鮑爾和戴維·羅默(1990)[u] 表明,實際的剛性可以與名義剛性相互作用,從而造成顯著的不平衡。 真正的僵化發生在企業緩慢調整其實際價格以應對經濟環境變化時。 例如,如果一家公司擁有市場力量,或者其投入成本和工資成本被合同鎖定,它可能會面臨真正的僵化。鮑爾和羅默認為,勞動力市場的真實剛性使得企業的成本保持高位,這使得企業猶豫降價並損失收入。 由實際剛性造成的費用加上更改價格的菜單成本,使得公司不太可能將價格降至市場清算水平。[144]
協調失敗
[編輯]
協調失敗是經濟衰退和失業的另一個潛在解釋。在經濟衰退期間,即使有人願意在其中工作,也有人願意購買工廠的生產,工廠仍然可以閒置。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衰退似乎是協調失敗的結果: 無形之手無法協調通常最優的生產和消費流程。羅素·庫珀和安德魯·約翰(1988)[v]表達了一種通用的協調形式,作為具有多重均衡的模型,代理可以在其中協調以改善(或至少不損害)各自的情況。庫珀和約翰的工作基於早期模型,包括彼得·戴蒙德(1982年)[w]的椰子模型,該模型展示了一個涉及搜索和匹配理論的協調失敗案例。在戴蒙德的模型中,如果生產商看到其他人生產,他們更有可能進行生產。 潛在貿易夥伴的增加提高了某個生產商找到交易對象的可能性。 與其他協調失敗的情況一樣,戴蒙德模型具有多重均衡,一個代理的福利取決於其他代理的決策。戴蒙德的模型是一個"厚市場外部性"的例子,當更多的人和企業參與其中時,市場會運作得更好。其他潛在的協調失敗來源包括自我實現的預言。 如果一家公司預計需求會下降,他們可能會減少招聘。 職位空缺的缺乏可能會讓工人擔憂,從而減少他們的消費。 這次需求的下降符合公司的預期,但完全歸因於公司的自身行為。[152]
勞動力市場失敗
[編輯]新凱恩斯主義者解釋了勞動力市場未能清理的原因。 在瓦爾拉斯市場中,失業工人壓低工資,直到對工人的需求滿足供應。如果市場是瓦爾拉斯式的,失業者的數量將僅限於在工作中轉換的工人以及因工資太低而無法吸引他們的工人。他們提出了幾種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市場可能會讓願意工作的工人失業。在這些理論中,新凱恩斯主義者特別與效率工資以及用於解釋先前失業長期影響的內部外部模型相關,即短期內的失業增加變得永久化,並在長期內導致更高的失業率。[161]
自然科學-outsider模型
[編輯]經濟學家對滯後現象產生了興趣,因為失業率在1979年石油危機和20世紀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中急劇上升,但沒有回到之前被認為是自然率的較低水平。奧利維爾·布蘭查德和勞倫斯·薩默斯(1986)[x]用內部外部模型解釋了失業中的滯後現象,這些模型也由阿薩爾·林德貝克和丹尼斯·斯諾爾在一系列論文和隨後出版的書中提出。[y] 內部人士,即已經在公司工作的員工,只關心自己的福祉。 他們寧願保持高工資,也不願減薪擴大就業。 失業的外來者在工資談判過程中沒有任何發言權,因此他們的利益沒有得到代表。 當失業率上升時,外來人員的數量也會增加。 即使經濟已經復甦,外部人士仍然被排除在談判過程之外。由經濟收縮期產生的更大範圍的外部人員池可能導致失業率持續上升。勞動力市場的滯後現象也提高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重要性。 如果經濟的暫時性衰退可以導致長期失業率上升,那麼穩定政策不僅提供暫時的緩解,還能防止短期衝擊演變成長期的失業率上升。[164]
效率工資
[編輯]
在效率工資模型中,工人的薪酬水平是最大化生產力而不是清空市場。例如,在開發中國家,企業可能會支付超過市場標準的費用,以確保員工能夠負擔足夠的營養以實現生產。公司也可能支付更高的工資以增加忠誠度和士氣,這可能帶來更好的生產力。企業也可以支付高於市場工資以防止逃稅。[167] 逃避現實的模式尤其具有影響力。卡爾·夏皮羅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84)[z] 創建了一個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員工傾向於避免工作,除非公司能夠監控員工的努力並威脅要解僱那些懶散的員工。如果經濟達到充分就業,被解僱的逃課者就會簡單地換一份新工作。個別公司支付給員工高於市場價格的溢價,以確保員工更願意工作並保留當前的工作,而不是逃避責任,冒險換一份新工作。 由於每家公司支付的工資都超過了市場清算工資,因此合併後的勞動力市場未能得到清算。 這導致了一大批失業工人,並增加了被解僱的成本。 工人不僅面臨工資下降的風險,他們還可能陷入失業者的困境。 將工資保持在市場清算水平以上會嚴重抑制逃避責任的動機,即使這會讓一些願意工作的工人失業,也能提高工人的效率。[169]
新增長理論
[編輯]更多信息: 內生增長理論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對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研究之後,直到1985年才進行了少量關於經濟增長的研究。保羅·羅默的論文[aa][ab]在激發生長研究的復興方面特別有影響力。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到90年代初蓬勃發展,許多宏觀經濟學家將注意力轉向了長期發展,並開始了包括內生增長在內的"新增長"理論。增長經濟學家試圖解釋一些實證事實,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未能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東亞虎組織的繁榮以及在20世紀90年代科技繁榮之前美國生產率增長的放緩。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下,增長率趨同已被預測,這一明顯的預測失敗激發了對內生增長的研究。[172]
三種新的增長模式家族挑戰了新古典主義模型。第一個挑戰了先前模型關於資本的經濟效益會隨時間減少的假設。 這些早期的新增長模式融入了資本積累的正面外部性,即一家公司在技術上的投資會因為知識的傳播而為其他公司帶來溢出效應。第二個重點在於創新在增長中的作用。 這些模型側重於通過專利和其他激勵措施來鼓勵創新的必要性。第三組被稱為"新古典主義復興",它將外生增長理論中對資本的定義擴展到包括人力資本。這項研究始於曼昆、羅默和韋爾(1992年)[ac] which showed that 78% of the cross-country variance in growth could be explained by a Solow model augmented with human capital.[6],結果顯示,78%的跨國增長差異可以用增強人力資本的索洛模型來解釋。[180]
內生增長理論認為,國家可以通過一個鼓勵其他國家技術與思想流入的開放社會實現快速的"追趕"增長。內生增長理論還建議,政府應該介入以鼓勵對研究和開發的投資,因為私營部門可能不會以最優水平進行投資。[181]
新的綜合
[編輯]主條目: 新古典主義綜合理論

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一種"新綜合"或"新古典綜合",它融合了新凱恩斯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思想。[182] 從新古典學派出發,它採納了紅血球假設,包括理性預期和方法;[183] 從新凱恩斯學派出發,它採用了名義剛性(價格粘性)[150]和其他市場不完善之處。新的綜合理論表明,貨幣政策可以對經濟產生穩定作用,這與新古典理論相反。新的綜合理論被學術經濟學家採納,很快也被中央銀行家等政策制定者採納。[150]
在綜合分析下,辯論已經變得不那麼意識形態化(涉及基本方法論問題),而是更加實證化。 伍德福德描述了這一變化:[187]
有時對外人來說,宏觀經濟學家在經驗方法論問題上似乎存在深刻分歧。 關於個別經驗主張的可信度,仍然存在,並且可能永遠都會存在激烈的分歧。 各種經驗方法被用於數據特徵描述和結構關係的估計,研究人員對特定方法的偏好各不相同,這通常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採用涉及更具體先驗假設的方法。 但這樣的辯論的存在不應掩蓋在更基本的方法問題上達成的廣泛共識。 無論是"校準主義者"還是貝葉斯估計的實踐者,都認同進行"定量理論"的重要性,並且都認可純粹數據特徵描述與結構模型驗證之間的區別。 並且兩者對可以被視為結構的模型形式有著相似的理解。
伍德福德強調,現在數據特徵化作品與結構模型之間有了更強的區別,後者不聲稱其結果與特定經濟決策之間的關係,而結構模型則試圖描述具有理論基礎的實際關係和經濟行為者所做的決策。 結構模型的驗證現在要求其規格反映"家庭或企業面臨的明確決策問題"。 伍德福德表示,數據特徵分析在"建立結構模型應解釋的事實"方面被證明是有用的,但不應作為政策分析的工具。 而是結構模型,通過代理人的實際決策來解釋這些事實,構成了政策分析的基礎。[187]
新的合成理論發展了稱為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紅血球模型,這些模型避免了盧卡斯批評。分布式發電模型提出了關於企業和家庭行為及偏好的假設;並計算了由此產生的分布式發電模型的數值解。這些模型還包括一個由經濟衝擊產生的"隨機"元素。 在最初的紅血球模型中,這些衝擊僅限於技術變革,但更近期的模型已經包含了其他實際的變化。計量經濟分析表明,實際因素有時會影響經濟。 弗蘭克·斯梅茨和拉斐爾·沃爾特斯(2007年)[ad]的一篇論文指出,貨幣政策只能解釋經濟產出波動的一小部分。在新的綜合模型中,衝擊可以同時影響需求和供給。[185]
最近,新的綜合模型的發展包括開發用於貨幣政策優化的異質代理模型:這些模型考察了在人群中擁有不同儲蓄行為的消費者群體對貨幣政策通過經濟傳遞的影響。[193]
2008年金融危機、大衰退與共識的演變
[編輯]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經濟大衰退挑戰了當時的短期宏觀經濟。很少有經濟學家預測到這場危機,即使在那之後,對於如何應對它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新的綜合理論形成於大緩和時期,並且尚未在嚴重的經濟環境中進行測試。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危機源於經濟泡沫,但綜合分析中的兩大宏觀經濟學派都沒有太關注金融或資產泡沫理論。當時宏觀經濟理論未能解釋這場危機,這促使宏觀經濟學家重新評估他們的思維方式。[197] 評論嘲笑了主流,並提出了重大重新評估。[198]
危機期間的特別批評針對的是在新綜合分析之前和期間開發的分布式帳本技術模型。 羅伯特·索洛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表示,政府專家組的模型"對反衰退政策沒有任何有用的見解,因為它在其本質上不可信的假設中構建了一個'結論',即宏觀經濟政策無能為力。"索洛還批評了分布式帳本技術模型,該模型經常假設單一的、"代表性代理"可以代表構成現實世界的多種不同代理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羅伯特·戈登在1978年後批評了許多宏觀經濟學。 戈登呼籲更新不平衡理論和非平衡建模。 他貶低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市場已經明朗;他還呼籲更新經濟模型,這些模型可以分別包括市場清算和粘性定價商品,如石油和住房。[201]
對分布式帳本技術模型的信心危機並沒有拆解新綜合模型所體現的更深層次共識,[ae][7][187]以及能夠解釋新數據持續發展的模型。 那些曾受到更多公眾和政治關注的領域,如收入不平等,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同時,那些包含顯著異質性的模型(與早期的通用數據分析模型不同)也受到了更多的關注。里卡多·卡巴列羅在批評政府專家組模型的同時,認為金融領域的研究顯示出進步,並建議現代宏觀經濟學需要重新定位,但不應在金融危機後被廢除。2010年,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納拉亞娜·科切拉科塔承認,奇異模型對於分析2007年至2010年的金融危機"不是非常有用"。 但認為這些模型的適用性正在"提高",並聲稱宏觀經濟學家們越來越達成共識,即通用數據倉庫模型需要同時包含"價格黏性和金融市場摩擦"。儘管他批評了分布式帳本技術建模,但他表示現代模型是有用的:
在21世紀初,...對於價格粘滯[af]的現代宏觀模型而言,擬合問題消失了。 弗蘭克·斯梅茨和拉夫·沃特斯使用新穎的貝葉斯估計方法證 明,一個足夠豐富的新凱恩斯模型能夠很好地擬合歐洲數據。 他們的發現,連同其他經濟學家的類似工作,導致了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在全球中央銀行的政策分析和預測中被廣泛採用。[206]
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教授查里在2010年表示,最先進的分布式發電模型允許行為和決策存在顯著的異質性,這些因素包括年齡、先前經驗和可用信息。[207] 在改進分布式帳本技術建模的同時,工作還包括開發經濟特定方面的異構代理模型,如貨幣政策傳導。[193][202]
環境問題
[編輯]
從21世紀開始,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自然環境和健康生態系統為人類帶來的益處)在經濟學中得到了更廣泛的研究。氣候變化也被更廣泛地認可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引發了關於經濟學中可持續發展的辯論。 氣候變化也已成為例如歐洲中央銀行政策的一個因素。
生態經濟學在21世紀也變得更加流行。在他們的宏觀經濟模型中,經濟系統是環境的一個子系統。 在這個模型中,生態經濟學中的收入循環流動圖被一個更複雜的流程圖所取代,該流程圖反映了太陽能的輸入,太陽能維持著自然輸入和環境服務,並將其用作生產單位。 一旦消耗掉,天然投入物就會以污染和廢物的形式從經濟中排出。 環境提供服務和材料的潛力被稱為"環境源功能",當資源被消耗或污染這些資源時,這一功能就會耗盡。 "匯功能"描述了環境吸收和傳遞無害廢物及污染的能力:當廢物輸出超過匯功能的極限時,就會造成長期損害。[209]: 8
另一個生態經濟學模型的例子是經濟學家凱特·拉沃思提出的甜甜圈模型。 這個宏觀經濟模型包括行星邊界,比如氣候變化。 這些來自生態經濟學的宏觀經濟模型雖然更受歡迎,但並未被主流經濟思想完全接受。
異端理論
[編輯]主條目: 非主流經濟學
非主流經濟學家堅持那些足夠脫離主流的理論,以至於被邊緣化,並被建制派視為無關緊要。最初,包括瓊·羅賓遜在內的非主流經濟學家與主流經濟學家合作,但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非主流團體自我孤立,形成了孤立的群體。當今的非主流經濟學經常在自己的期刊上發表論文,而不是主流期刊上,並且他們避免正式的建模,轉而從事更抽象的理論工作。[210]
根據《經濟學人》報道,2008年的金融危機及隨後的經濟衰退凸顯了當時宏觀經濟理論、模型和計量經濟學的局限性。當時的大眾媒體討論了後凱恩斯經濟學和奧地利經濟學,這兩種非主流傳統對主流經濟學影響不大。[215][216]
後凱恩斯經濟學
[編輯]主條目: 後凱恩斯經濟學
雖然新凱恩斯主義者將凱恩斯的思想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相結合,後凱恩斯主義者則朝其他方向發展。 後凱恩斯主義者反對新古典主義的綜合理論,並認同一種原教旨主義的凱恩斯解釋,該解釋旨在發展沒有古典元素的經濟理論。後凱恩斯主義信仰的核心是拒絕古典和主流凱恩斯觀點中的三個核心公理:貨幣的中立性、總替代性和遍歷公理。[218][219] 後凱恩斯主義者不僅在短期內拒絕金錢的中立性,還將金錢視為長期的重要因素,而其他凱恩斯主義者在20世紀70年代就放棄了這種觀點。 總替代意味著商品是可以互換的。 相對價格的變化導致人們根據變化的比例調整他們的消費。遍歷公理認為,可以根據過去和當前的市場條件來預測經濟的未來。 沒有遍歷假設,智能體無法形成理性預期,從而削弱了新經典理論。在非彈性經濟中,預測非常困難,決策受到不確定性的阻礙。 部分由於不確定性,後凱恩斯主義者在粘性價格和工資問題上的立場與新凱恩斯主義者不同。 他們不認為名義上的僵化是市場未能澄清的原因。 他們認為粘性價格和長期合同是穩定預期並緩解阻礙有效市場的不確定性。後凱恩斯經濟政策強調需要減少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包括安全網和價格穩定。海曼·明斯基將後凱恩斯主義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概念應用於金融危機理論中,在這種理論中,投資者越來越多地承擔債務,直到他們的回報無法再支付槓桿資產的利息,從而導致了金融危機。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明斯基的工作引起了主流關注。[214]
奧地利商業周期理論
[編輯]主條目: 奧地利商業周期理論

奧地利經濟學派起源於卡爾·門格爾871年的《經濟學原理》。 門格的追隨者們形成了一群獨立的經濟學家,直到大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地利經濟學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區別基本上已經瓦解。 然而,奧地利的傳統通過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作品得以保存下來,成為一個獨特的學派。 現代的奧地利人以其對早期奧地利作品的興趣以及避免使用包括計量經濟學在內的標準經驗方法而著稱。 奧地利人也關注市場過程而不是均衡。主流經濟學家通常對其方法論持批評態度。[224][225]
哈耶克創立了奧地利商業周期理論,該理論結合了門格爾的資本理論和米塞斯的貨幣與信貸理論。該理論提出了一種跨時期投資模型,其中生產計劃先於最終產品的製造。 生產商調整生產計劃以適應消費者偏好的變化。生產者回應的是"衍生需求",即對未來需求的估計,而不是當前的需求。 如果消費者減少支出,生產者認為消費者正在為以後的額外支出儲蓄,從而使生產保持不變。結合可貸款資金市場(通過利率將儲蓄和投資聯繫起來),這一資本生產理論導致了一個宏觀經濟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市場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偏好。哈耶克的模型表明,當廉價信貸引發資源錯配的繁榮時,經濟泡沫就開始了,導致生產早期階段獲得超出預期的資源,從而開始過度生產;而後期資本則沒有資金用於維護以防止貶值。早期的過度生產不能通過後期維護不善的資本來處理。 當成品短缺導致"強制儲蓄",因為可供銷售的成品減少了時,繁榮就變成了蕭條。[230]
注釋
[編輯]- ^ Hicks, J. R.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April 1937, 5 (2): 147–159. JSTOR 1907242. doi:10.2307/1907242.
- ^ Modigliani, Franco.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 Money. Econometrica. January 1944, 1 (12): 45–88. JSTOR 1905567. doi:10.2307/1905567.
- ^ Solow, Robert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56, 70 (1): 65–94. JSTOR 1884513. doi:10.2307/1884513. hdl:10338.dmlcz/143862
 .
.
- ^ Swan, 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1956, 32 (2): 334–361. doi:10.1111/j.1475-4932.1956.tb00434.x.
- ^ Phillips, A. W.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November 1958, 25 (100): 283–299. JSTOR 2550759. doi:10.2307/2550759.
- ^ Clower, Robert W. The Keynesian Counter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Hahn, F. H., F.H.; Brechling, F. P.R. (編).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London: Macmillan. 1965.
- ^ Leijonhufvud, Axel.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 a study in monetary the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ISBN 978-0-19-500948-4.
- ^ Barro, Robert J.; Grossman, Herschel I. 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 61 (1): 82–93. JSTOR 1910543.
- ^ Leijonhufvud, Axel.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 a study in monetary the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ISBN 978-0-19-500948-4.
- ^ Malinvaud, Edmond.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considered. Yrjö Jahnsson lectures.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1977. ISBN 978-0-631-17350-2. LCCN 77367079. OCLC 3362102.
- ^ Friedman, Milto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 Restatement. Friedman, Milton (編).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 ^ Lucas, Robert E.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2, 4 (2): 103–123. CiteSeerX 10.1.1.592.6178
 . doi:10.1016/0022-0531(72)90142-1.
. doi:10.1016/0022-0531(72)90142-1.
- ^ Muth, John 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 Econometrica. 1961, 29 (3): 315–335. JSTOR 1909635. doi:10.2307/1909635.
- ^ Sargent, Thomas J.; Wallace, Neil. '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Optimal Monetary Instrument,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5, 83 (2): 241–54. JSTOR 1830921. S2CID 154301791. doi:10.1086/260321.
- ^ Hall, Robert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 (6): 971–987. JSTOR 1840393. S2CID 54528038. doi:10.1086/260724.
- ^ Lucas, Robert.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Brunner, K.; Meltzer, A. (編).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 New York: American Elsevier. 1976: 19–46. ISBN 978-0-444-11007-7.
- ^ Lucas, R.E.; Rapping, L.A. Real Wages,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 77 (5): 721–754. JSTOR 1829964. S2CID 154683563. doi:10.1086/259559.
- ^ Lucas, R. E.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 (3): 326–334. JSTOR 1914364.
- ^ Kydland, F. E.; Prescott, E. C.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 1982, 50 (6): 1345–1370. JSTOR 1913386. doi:10.2307/1913386.
- ^ Fischer, S. Long-Term Contract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85 (1): 191–205. S2CID 36811334. doi:10.1086/260551. hdl:1721.1/63894
 .
.
- ^ Ball, L.; Romer, D. Real Rigidities and the Non-Neutrality of Money (PDF).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0, 57 (2): 183–203. JSTOR 2297377. doi:10.2307/2297377.
- ^ Cooper, R.; John, A. Coordinating Coordination Failures in Keynesian Models (PDF).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 103 (3): 441–463 [11 July 2019]. JSTOR 1885539. doi:10.2307/1885539.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7 April 2019).
- ^ Diamond, Peter A.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in Search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2, 90 (5): 881–894. JSTOR 1837124. S2CID 53597292. doi:10.1086/261099. hdl:1721.1/66614
 .
.
- ^ Blanchard, O. J.; Summers, L. H. Hysteresis and the European Unemployment Problem.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86, 1: 15–78. JSTOR 3585159. doi:10.2307/3585159
 .
.
- ^ Lindbeck, Assar; Snower, Dennis. The insider-outsider theory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8. ISBN 978-0-262-62074-1.
- ^ Shapiro, C.; Stiglitz, J. E.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 (3): 433–444. JSTOR 1804018.
- ^ Romer, Paul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PDF).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 98 (5): S71–S102. JSTOR 2937632. S2CID 11190602. doi:10.1086/261725.
- ^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PDF).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 94 (5): 1002–1037. JSTOR 1833190. S2CID 6818002. doi:10.1086/261420.
- ^ Mankiw, N. Gregory; Romer, David; Weil, David N.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2, 107 (2): 407–437. CiteSeerX 10.1.1.335.6159
 . JSTOR 2118477. S2CID 1369978. doi:10.2307/2118477.
. JSTOR 2118477. S2CID 1369978. doi:10.2307/2118477.
- ^ Smets, Frank; Wouters, Rafael. Shocks and Frictions in US Business Cycles: A Bayesian DSGE Approach (PDF).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 (3): 586–606. S2CID 6352558. doi:10.1257/aer.97.3.586. hdl:10419/144322.
- ^ This consisting of: that macroeconomic analysis should use models with intertemporal and general-equilibrium foundations, that quantitative policy analysis should use econometrically validated structural models, that expectations should be modeled as endogenous, that real factors can cause shocks to both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at monetary policy is effective (as opposed to the view that it has no effects)
- ^ By the term "[statistical] fit", Kocherlakota is referring to the "model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that "were based on estimated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s, and so we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fit the existing data well." Kocherlakota (2010)
參考文獻
[編輯]- ^ Blanchard 2000,第1377頁.
- ^ Dimand 2008.
- ^ Dimand 2008. : p.69.
- ^ McCallum 2008..
- ^ Mankiw 2006. : pp.37–38.
- ^ Klenow & Rodriguez-Clare 1997,第73頁.
- ^ Woodford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