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A15928872517/"History of macroeconomic thought"
宏观经济思想史
[编辑]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宏观经济学理论起源于商业周期和货币理论的研究。[1][2]一般来说,早期的理论家认为货币因素不能影响实际产出等实际因素。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攻击了一些这些"经典"理论,并提出了一种通用理论,该理论将整个经济描述为总体而非单独的微观经济部分。 他试图解释失业和经济衰退,注意到在经济衰退期间,人们和企业倾向于囤积现金并避免投资。 他辩称,这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设,即市场总是清澈的,不会留下商品过剩和愿意劳动力的闲置。[3]
跟随凯恩斯的一代经济学家将他的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相结合,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的综合。 尽管凯恩斯理论最初省略了对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的解释,但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采用了菲利普斯曲线来模拟价格水平的变化。 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反对将凯恩斯的理论与均衡系统结合的综合方法,而是提倡非均衡模型。 以米尔顿·佛利民为首的货币主义者采纳了一些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比如对货币需求的重要性,但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忽视了货币供应在通货膨胀中的作用。[4]罗伯特·卢卡斯和其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批评了在理性预期下行不通的凯恩斯模型。 卢卡斯还辩称,凯恩斯的经验模型不会像基于微观经济基础的模型那样稳定。
新的古典学派最终形成了真实的商业周期理论。 像早期的经典经济模型一样,皇家银行模型假设市场已经明朗,并且商业周期是由技术和供应的变化驱动的,而不是需求。 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解决卢卡斯和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许多批评。 新凯恩斯主义者采纳了理性的预期,并建立了以粘性价格为微观基础的模型,这表明经济衰退仍然可以由需求因素解释,因为刚性阻止了价格降至市场清盘水平,从而留下了商品和劳动力的过剩。 新的新古典主义综合理论将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元素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共识。 其他经济学家回避了关于短期动态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辩论,发展了新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5]大衰退导致了该领域的现状回顾,一些公众的关注点转向了异端经济学。
起源
[编辑]
宏观经济学源自两个研究领域:商业周期理论和货币理论。货币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由马丁·德·阿斯皮尔库埃塔提出,而商业周期分析则始于19世纪中叶。
商业周期理论
[编辑]从19世纪60年代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克莱门特·朱格拉开始,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经济活动频繁且剧烈变化的周期。[9] 这一努力的一个关键里程碑是韦斯利·米切尔于1920年创立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这标志着经济波动理论统计模型(基于周期和趋势而非经济理论的模型)的繁荣的开始,这些模型导致了像库兹涅茨浪潮这样的看似规律的经济模式的发现。[10]
其他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商业周期分析中更侧重于理论。 大多数商业周期理论都集中在单一因素上,比如货币政策或天气对当时主要农业经济的影响。[8] 尽管商业周期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相当成熟,但丹尼斯·罗伯逊和拉尔夫·霍特里等理论家的工作对公共政策影响甚微。他们的部分均衡理论无法捕捉到市场相互作用的普遍均衡;特别是早期的商业周期理论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分开处理。[9] 这些领域的研究使用微观经济方法来解释就业、价格水平和利率。[12]
货币理论
[编辑]最初,价格水平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是由货币的数量理论解释的;大卫·休谟在他的1752年著作《货币论》(论文集,道德、政治和文学,第二部分,第三篇)中提出了这一理论。数量理论通过萨伊定律来审视整个经济,该定律指出,供应给市场的商品将会被出售——简而言之,市场总是清仓的。[3] 在这种观点下,货币是中立的,不能影响经济中的实际因素,如产出水平。 这与经典的二元观点一致,即经济的实际方面和名义因素,如价格水平和货币供应量,可以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向经济中添加更多资金只会提高价格,而不是创造更多的商品。[15]
货币的数量理论主导了宏观经济理论,直到20世纪30年代。 两个版本特别有影响力,一个是由欧文·费雪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等作品中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则由剑桥经济学家在20世纪初提出。费舍尔的数量理论可以通过保持货币流通速度(给定货币在交易中使用频率)和实际收入(质量)不变,并允许货币供应量(质量)和价格水平(质量)在交换方程中变化来表达:[16]
大多数古典理论,包括费舍尔的理论,都认为速度是稳定的,并且独立于经济活动。剑桥经济学家,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始挑战这一假设。 他们提出了剑桥现金平衡理论,该理论研究了货币需求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剑桥理论并不假设货币的需求和供给总是处于平衡状态,它解释了当经济下滑时人们持有更多现金的情况。 通过考虑持有现金的价值,剑桥经济学家朝着凯恩斯后来发展的流动性偏好概念迈出了重要一步。剑桥理论认为人们持有货币有两个原因:促进交易和维持流动性。 在后来的研究中,凯恩斯在他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中添加了第三个动机——投机,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他的通用理论。[19]
1898年,努特·维克塞尔提出了一种以利率为中心的货币理论。 他的分析使用了两种利率:由银行系统确定的市场利率和由资本回报率确定的实际或"自然"利率。在威克塞尔的理论中,当技术创新导致自然利率上升或银行系统允许市场利率下降时,累积通胀就会发生。 累积通缩发生在相反的情况下,导致市场利率升至自然水平以上。[2] 威克塞尔的理论并没有产生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直接关系。 根据威克塞尔的观点,只要自然货币超过市场利率,货币就会在内生中被创造出来,而硬通货的数量不会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人将利润转化为现金存入银行储备,从而扩大货币供应量。 这可能导致一个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胀持续上升而货币基础没有扩大。 威克尔的工作影响了凯恩斯和斯德哥尔摩学派中的瑞典经济学家。[21]
凯恩斯通论
[编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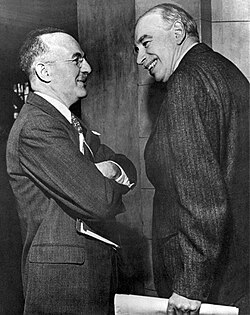
现代宏观经济学可以说始于凯恩斯,并于193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扩展了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并建立了一个关于经济运作的一般理论。 凯恩斯的理论首次将货币因素和实际经济因素结合起来,[9] 解释了失业问题,并提出了实现经济稳定的政策建议。[23]
凯恩斯认为经济产出与货币流通速度呈正相关。他通过改变流动性偏好来解释这种关系:人们在经济困难时期通过减少支出来增加资金持有量,这进一步放缓了经济增长。 这个节俭的悖论声称,个人在经济衰退中生存的努力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当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时,货币流通速度就会减慢。 经济活动放缓意味着市场可能无法清理,导致过剩商品浪费和产能闲置。凯恩斯颠覆了数量理论,认为市场变化会改变数量而不是价格。凯恩斯用固定价格水平的假设取代了稳定速度的假设。 如果支出减少而价格没有下降,商品的过剩会减少对工人的需求并增加失业率。[28]
古典经济学家难以解释非自愿失业和经济衰退,因为他们将萨伊定律应用于劳动力市场,并期望所有愿意以现行工资工作的人都能就业。在凯恩斯的模型中,就业和产出由总需求驱动,即消费和投资的总和。 由于消费保持稳定,总体需求的大多数波动都源于投资,而投资是由许多因素驱动的,包括预期、"动物精神"和利率。凯恩斯认为财政政策可以补偿这种波动。 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可以增加支出以购买过剩商品并雇用闲置劳动力。此外,乘数效应增加了这种直接支出的效果,因为新雇用的工人会花费他们的收入,这些收入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中,而企业则会投资以应对需求的增长。[25]
凯恩斯关于强烈公共投资的建议与他对不确定性的兴趣有关。凯恩斯在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一书中提供了对统计推断的独特视角,这比他的主要经济著作早了很多年。凯恩斯认为,强大的公共投资和财政政策可以抵消经济波动不确定性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虽然凯恩斯的继任者很少关注他工作中的概率部分,不确定性可能在一般理论的投资和流动性偏好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32]
凯恩斯工作的确切含义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 甚至凯恩斯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的解释,作为一般理论中较为明确的一部分,也成为了辩论的主题。 经济学家和学者们争论凯恩斯的建议是旨在通过重大政策转变来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还是通过适度保守的解决方案来处理一个小问题。[34]
凯恩斯的继任者
[编辑]凯恩斯的继任者们讨论了凯恩斯模型的确切表述、机制及其后果。 一组代表了凯恩斯的"正统"解释; 他们将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思想相结合,产生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初主导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者的两个阵营对这种对凯恩斯的综合解释提出了批评。 一组关注凯恩斯作品中的不平衡方面,而另一组则对凯恩斯持原教旨主义立场,并开始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异端传统。[37]
新古典综合理论
[编辑]主条目: 新古典综合
跟随凯恩斯的一代经济学家,即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相结合,创造了"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主义者处理了两个微观经济问题:首先,为凯恩斯理论的某些方面,如消费和投资奠定基础;其次,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相结合。[39] (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各个市场相互作用,如果存在完全竞争、没有外部性和完美信息,则存在均衡价格。)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1947年)为这一综合提供了大量的微观经济基础。萨缪尔森的工作为新凯恩斯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树立了典范:用正式的数学模型表达的经济理论。尽管凯恩斯的理论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他的继任者们大多放弃了他非正式的方法论,转而支持萨缪尔森的理论。[42]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停止了对凯恩斯主义的辩论,接受了综合观点;然而,仍然存在分歧的空间。综合分析将市场清理的问题归因于粘性价格,这些价格未能调整以适应供需的变化。另一组凯恩斯主义者专注于非均衡经济学,并试图在缺乏市场清算的情况下调和均衡的概念。[46]
新凯恩斯模型
[编辑]主条目: 新凯恩斯经济学

1937年,约翰·希克斯[a]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凯恩斯的思想纳入了一个总体均衡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下,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整体均衡中相遇。希克的"投资-储蓄/流动性偏好-货币供应"模型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数十年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基础。该模型用信息安全曲线表示商品市场,该曲线是一组代表投资和储蓄均衡的点。 货币市场均衡用货币模型曲线表示,该曲线是一组代表货币供需平衡的点。 曲线的交集识别了经济中的总体均衡[50],其中利率和经济产出具有唯一的均衡值。印度卢比模型侧重于将利率作为"货币传导机制",即货币供应影响总需求和就业等实际变量的渠道。 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减少投资并降低整个经济的产出。其他经济学家则基于信息系统/生命周期管理框架进行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1944年,法兰科·莫迪利安尼[b]增加了劳动力市场。 莫迪利亚尼的模型将经济描绘成一个在劳动、金融和商品等相互关联的市场中普遍均衡的系统,并用严格的名义工资来解释失业问题。[53]
增长曾引起亚当·斯密等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兴趣,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边缘主义革命期间,当研究人员专注于微观经济学时,研究工作逐渐减少。当新凯恩斯主义者罗伊·哈罗德和埃弗塞·多马独立发展哈罗德-多马模型时,经济增长的研究重新兴起。哈罗德-多马尔模型是将凯恩斯的理论扩展到长期领域,而凯恩斯自己对此也没有进行过研究。他们的模型结合了凯恩斯的乘数效应和投资加速器模型,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果: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率(资本总额除以产出总额)。哈罗德-多马尔模型主导了增长理论,直到1956年罗伯特·索洛[c]和特雷弗·斯旺[d]独立开发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和斯旺提出了一种更具经验吸引力的模型,该模型基于生产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替代,实现了"平衡增长"。索洛和斯旺建议,增加储蓄只能暂时促进经济增长,而只有技术改进才能在长期内增加增长。在索洛和斯旺之后,从1970年到1985年,增长研究逐渐减少,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增长的研究。[55]
经济学家将综合理论工作融入到大规模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中,该模型结合了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等因素的个别方程与经验观测数据。这项研究在莫迪利亚尼及其合作者开发的麻省理工学院-宾大-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模型下达到了顶峰。[61] 宏观经济学结合了信息素养与其他方面的综合分析,包括新古典增长模型和通胀与产出之间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大型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都成为了综合理论批评者的目标。
菲利普斯曲线
[编辑]主条目: 菲利普斯曲线

凯恩斯并没有明确阐述价格水平的理论。早期的凯恩斯模型假设工资和其他价格水平是固定的。这些假设在20世纪50年代通胀稳定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60年代中期,通胀率上升,并成为宏观经济模型的问题。1958年,威廉·菲利普斯[e]提出了一个价格水平理论的基础,他实证观察到通货膨胀和失业似乎呈反比关系。 1960年,理查德·利普西{{efn|Lipsey, R.G.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2–1957: A Further Analysis. Economica. February 1960, 27 (105): 1–31. JSTOR 2551424. doi:10.2307/2551424.首次提供了这一相关性的理论解释。 一般来说,凯恩斯主义对曲线的解释认为,过剩的需求推动了高通胀和低失业率,而产出缺口则提高了失业率并抑制了物价。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菲利普斯曲线面临着实证和理论方面的攻击。 曲线所代表的产出与通胀之间的假设权衡是凯恩斯体系中最薄弱的部分。[69]
失衡的宏观经济学
主条目: 失衡的宏观经济学
尽管新古典主义综合理论盛行,但它也有凯恩斯主义的批评者。 一种不平衡或"非瓦尔拉斯"理论被提出[70],该理论批评这种综合理论在允许不平衡现象,特别是非自愿失业,在平衡模型中建模时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外,他们认为,一个市场的失衡必须与另一个市场的失衡相关联,因此非自愿失业必须与商品市场的过剩供应挂钩。 许多人认为唐·帕廷金的作品是失衡领域中的第一部。罗伯特·克洛尔(1965)[f]提出了他的"双重决策假说",即市场中的人可能决定自己想买什么,但最终他的购买量取决于他能卖出多少。克洛尔和阿克塞尔·莱昂胡夫德(1968)[g]认为,不平衡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部分,值得更多的关注。罗伯特·巴罗和赫歇尔·格罗斯曼提出了普遍的非均衡模型[h],在这些模型中,个别市场在形成普遍均衡之前就已经锁定在价格中。 这些市场产生了"虚假价格",导致了失衡。巴罗和格罗斯曼的工作不久后,不平衡模型在美国失宠了,巴罗放弃了凯恩斯主义,采纳了新的经典市场清算假设。[78]凯恩斯并没有明确阐述价格水平的理论。早期的凯恩斯模型假设工资和其他价格水平是固定的。这些假设在20世纪50年代通胀稳定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60年代中期,通胀率上升,并成为宏观经济模型的问题。1958年,菲利普斯提出了一个价格水平理论的基础,他实证观察到通货膨胀和失业似乎呈反比关系。 1960年,理查德·利普西首次提供了这一相关性的理论解释。 一般来说,凯恩斯主义对曲线的解释认为,过剩的需求推动了高通胀和低失业率,而产出缺口则提高了失业率并抑制了物价。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菲利普斯曲线面临着实证和理论方面的攻击。 曲线所代表的产出与通胀之间的假设权衡是凯恩斯体系中最薄弱的部分。[69]
失衡的宏观经济学
[编辑]主条目: 失衡的宏观经济学 尽管新古典主义综合理论盛行,但它也有凯恩斯主义的批评者。 一种不平衡或"非瓦尔拉斯"理论被提出[70],该理论批评这种综合理论在允许不平衡现象,特别是非自愿失业,在平衡模型中建模时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外,他们认为,一个市场的失衡必须与另一个市场的失衡相关联,因此非自愿失业必须与商品市场的过剩供应挂钩。 许多人认为唐·帕廷金的作品是失衡领域中的第一部。罗伯特·克洛尔(1965)提出了他的"双重决策假说",即市场中的人可能决定自己想买什么,但最终他的购买量取决于他能卖出多少。克洛尔和阿克塞尔·莱昂胡夫德(1968)[i]认为,不平衡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部分,值得更多的关注。罗伯特·巴罗和赫歇尔·格罗斯曼提出了普遍的非均衡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个别市场在形成普遍均衡之前就已经锁定在价格中。 这些市场产生了"虚假价格",导致了失衡。巴罗和格罗斯曼的工作不久后,不平衡模型在美国失宠了,巴罗放弃了凯恩斯主义,采纳了新的经典市场清算假设。[78]

虽然美国经济学家很快放弃了非均衡模型,欧洲经济学家则更愿意接受没有市场清算的模型。像埃德蒙·马林瓦德和雅克·德雷兹这样的欧洲人扩展了不平衡的传统,并努力解释价格刚性,而不是简单地假设它。马林沃德(1977)[j] 利用不平衡分析发展了一种失业理论。他辩称,劳动和商品市场的失衡可能导致商品和劳动力的配给,从而引发失业。马林瓦德采纳了固定价格框架,并认为与主导农业经济的相对灵活的原材料定价系统相比,现代工业价格的定价将较为僵化。[82] 价格固定,仅限数量调整。马林沃德认为,在古典和凯恩斯失业的情况下,达到均衡状态的可能性最大。[83] 新古典主义传统中的工作被限制为马林沃德类型学的一个特例,即瓦尔拉斯均衡。 在马林沃的理论中,由于工业定价的性质,几乎不可能达到瓦尔拉斯均衡情况。[83]
货币主义
[编辑]主条目: 货币主义
米尔顿·佛利民提出了一种替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最终被标记为货币主义。 一般来说,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应对宏观经济很重要。当货币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时,凯恩斯主义者忽视了金钱在通货膨胀和商业周期中的作用,而货币主义直接挑战了这些观点。[4]
批评和增强菲利普斯曲线
[编辑]菲利普斯曲线似乎反映了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明显的逆向关系。 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同时陷入停滞和被称为滞胀的通货膨胀,曲线崩溃了。 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性崩溃紧随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费尔普斯基于理论发起的攻击之后。 尽管菲尔普斯不是货币主义者,但他认为只有意外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才会影响就业。 菲尔普斯的"期望增强菲利普斯曲线"的各种变体成为了标准工具。 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使用了没有长期通胀和失业之间权衡的模型。 他们使用了基于自然失业率的模型,而不是菲利普斯曲线,在这种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只能暂时将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以下。 最终,企业会根据实际因素调整其价格和工资以应对通货膨胀,忽略货币政策的名义变化。 扩张性的推动将被抹去。[85]
金钱的重要性
[编辑]安娜·施瓦茨与弗里德曼合作,创作了货币主义的重要作品之一《美国货币史》(1963年),该作品将货币供应与商业周期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者基于大萧条期间利率极低但产出仍然低迷的证据,采纳了货币政策不会影响总产出或商业周期的观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只关注名义利率,而忽视了通货膨胀在大萧条期间一直较高的实际利率中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紧缩的,对产出和就业施加了下行压力,尽管经济学家仅从名义利率来看认为货币政策具有刺激性。[88]
弗里德曼发展了自己的货币数量理论,该理论参考了欧文·费雪的理论,但继承了凯恩斯的许多观点。弗里德曼1956年的《货币数量理论:重述》[k] 将凯恩斯对货币的需求和流动性偏好纳入了一个类似于经典交换方程的方程中。弗里德曼更新的数量理论也允许使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来解决重大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弗里德曼与凯恩斯决裂,他认为即使在经济衰退期间,货币需求也相对稳定。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微调"是适得其反的。 他们发现,即使在财政政策调整期间,货币需求也保持稳定,[92] 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存在滞后现象,这使得它们过于缓慢,无法防止轻微的经济下滑。[93]
突出与衰落
[编辑]
货币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吸引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版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在滞胀期间表现更好,增强了货币主义的可信度。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已成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新正统观念,到了70年代末,英国和美国的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大多采纳了以货币供应为目标而非利率的货币主义政策。然而,由于测量难度,中央银行很难瞄准货币总量。[98] 1979年保罗·沃克接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货币主义面临着重大考验。 沃尔克收紧了货币供应量,降低了通货膨胀,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降低了货币主义的受欢迎程度,但清楚地展示了货币供应在经济中的重要性。[4] 当曾经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主义的预测相悖,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出现波动时,货币主义的可信度降低了。[94] 货币主义的单等式模型和绘图数据非统计分析方法也输给了凯恩斯主义者青睐的同时等式建模。[99] 货币主义的政策和分析方法在中央银行家和学者中失去了影响力,但其核心原则是货币的长期中立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会对实际变量产生长期影响)以及使用货币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甚至在凯恩斯主义者中也成为了宏观经济主流的一部分。[4][98]
新古典经济学
[编辑]主条目: 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从货币主义演变而来,并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其他挑战。 早期的新古典主义者认为自己是货币主义者,[101] 但新古典学派逐渐发展起来。 新古典主义者放弃了货币政策能够系统性影响经济的货币主义信念,[102] 最终采纳了完全忽略货币因素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103]
新古典主义完全打破了凯恩斯经济理论,而货币主义者则建立在凯恩斯主义思想之上。尽管抛弃了凯恩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分享了凯恩斯主义对解释短期波动的关注。 新古典主义取代货币主义者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对手,并将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辩论从是否关注短期波动转变为宏观经济模型是否应基于微观经济理论。像货币主义一样,新古典经济学也根植于芝加哥大学,主要是由小罗伯特·卢卡斯创立的。 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其他领军人物包括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103]
新古典经济学家写道,早期的宏观经济理论仅勉强基于微观经济理论,并将其努力描述为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 新古典主义者也引入了理性预期,并认为鉴于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政府几乎没有能力稳定经济。 最具争议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重新提出了市场清算的假设,他们既假设价格具有灵活性,也认为市场应该以均衡状态进行建模。[106]
理性预期与政策无关性
[编辑]
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认识到,人们的经济决策基于对未来的预期。 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模型都依赖于自适应预期,这种预期基于过去趋势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在一段时间内通胀率平均为4%,经济主体被假设预期第二年的通胀率为4%。1972年,[l]在约翰·穆斯[m]1961年的一篇农业经济学论文的影响下,卢卡斯将理性预期引入了宏观经济学。本质上,适应性预期将行为建模为回顾性,而理性预期则建模为前瞻性的经济主体(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新古典经济学家还声称,如果一个经济模型假设其所建模的代理行为好像他们不知道该模型的存在,那么该模型在内部将是不一致的。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下,模型假设代理基于模型本身的最优预测进行预测。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具有完美的远见,而是他们基于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深入理解行事。[114]
汤玛斯·萨金特和尼尔·华莱士(1975)[n]将理性预期应用于菲利普斯曲线中通胀与产出之间的模型,发现货币政策无法系统地稳定经济。 萨金特和华莱士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发现,经济主体会在货币刺激措施增加就业和产出之前,预测通货膨胀并调整到更高的价格水平。只有未预期的货币政策才能增加就业,而且没有任何中央银行能够在没有经济主体在价格变化产生刺激性影响之前,系统地利用货币政策进行扩张。[116]
罗伯特·埃。[o] 霍尔将理性预期应用于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即人们当前的消费水平基于他们的财富和终身收入,而不是当前收入。霍尔发现,人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滑他们的消费,并且只有在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发生变化时才会改变消费模式。霍尔和弗里德曼关于永久收入假说的版本都挑战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即像减税这样的短期稳定政策可以刺激经济。永久收入观点认为消费者应以财富为基础进行消费,因此收入的暂时增长只会产生适度的消费增加。经验测试表明,霍尔假设可能低估了由于收入增加而导致的消费增长;然而,霍尔的工作帮助普及了欧拉消费方程模型。[119]
卢卡斯批判与微观基础
[编辑]1976年,卢卡斯撰写了一篇论文[p],批评用于预测和政策评估的大规模凯恩斯模型。 卢卡斯认为,基于变量之间经验关系的经济模型在政策变化时是不稳定的:在一个政策制度下,关系可能在制度变化后失效。卢卡斯的批评更进一步,认为政策的影响取决于该政策如何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 没有模型是稳定的,除非它考虑了预期以及预期如何与政策相关。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放弃凯恩斯主义的不均衡模型,专注于基于结构和行为的均衡模型可以纠正这些缺陷。凯恩斯经济学家通过建立基于稳定理论关系的微观基础模型作出了回应。[122]
卢卡斯供给理论和商业周期模型
[编辑]参见: 卢卡斯群岛模型
卢卡斯和伦纳德·雷平[q]在1969年首次提出了新的古典总量供给方法。 在他们的模型中,就业的变化基于工人对闲暇时间的偏好。 卢卡斯和雷平将就业减少建模为工人自愿选择减少工作努力,以应对当前的工资水平。[123]
卢卡斯(1973)[r] 提出了一种基于理性预期、不完美信息和市场清算的商业周期理论。 在构建这个模型时,卢卡斯试图纳入一个经验事实,即通货膨胀和产出之间存在权衡,同时不妥协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这个模型包含了货币惊喜的概念:货币政策只有在人们因商品价格相对变化而感到惊讶或困惑时才重要。卢卡斯假设生产者会在认识到其他行业的变化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自己行业的变化。 基于这一假设,生产者可能会将整体价格水平的提高视为对其商品需求的增加。 生产商通过增加产量来回应,却发现整个经济中的价格普遍上涨,而不是专门针对他的商品。这个"卢卡斯供给曲线"模型的输出取决于"价格"或"货币惊喜",即预期通胀与实际通胀之间的差异。卢卡斯的"惊喜"商业周期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失宠,因为实证证据未能支持这一模型。[127][128]
实际商业周期理论
[编辑]
尽管"金钱惊喜"模式受挫,但仍继续努力开发一个新的经典商业周期模型。 1982年,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s]发表的一篇论文介绍了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商业周期完全可以由供给侧来解释,模型表示的是系统处于恒定平衡状态的经济。皇家银行忽视了用价格惊喜、市场失灵、价格粘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来解释商业周期的必要性。相反,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构建了简洁的模型,这些模型通过技术和生产力的变化来解释商业周期。就业水平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些技术和生产力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就业欲望。皇家银行拒绝了经济衰退期间高非自愿失业率的想法,不仅否定了金钱能够稳定经济的观点,也否定了货币主义认为金钱可以破坏经济稳定的观点。[132]
真正的商业周期建模者寻求基于箭头-德布罗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来构建宏观经济模型。红细胞模型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灵感来源之一。 分布式账本技术模型已成为宏观经济学家常用的方法论工具,即使是那些不同意新古典理论的人也是如此。[129]
新凯恩斯经济学
[编辑]主条目: 新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指出了新古典综合理论内在的矛盾: 瓦尔拉斯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清算和一般均衡理论不能导致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市场未能清算的情况。 新凯恩斯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一悖论,但新古典主义者放弃了凯恩斯,而新凯恩斯主义者则放弃了瓦尔拉斯和市场清理。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新凯恩斯研究人员调查了市场不完善(如垄断竞争)、名义摩擦(如粘性价格)以及其他摩擦如何使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保持一致。新凯恩斯主义者经常制定具有理性预期的模型,这些模型由卢卡斯提出,并被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纳。[139]
名义刚度和实际刚性
[编辑]斯坦利·费希尔(1977)[t] 回应了汤玛斯·萨金特和尼尔·华莱士的货币无效性命题,并展示了货币政策如何即使在具有理性预期的模型中也能稳定经济。费舍尔的模型展示了在长期名义工资合同模型中,货币政策如何产生影响。[140] 约翰·B·泰勒进一步阐述了费希尔的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可能产生长期影响——即使在工资和价格调整之后也是如此。 泰勒通过基于费舍尔的模型,假设合同谈判是分阶段进行的,并且合同在较长时期内固定名义价格和工资率,得出了这一结果。这些早期的新凯恩斯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理念:给定固定的名义工资,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可以控制就业率。由于工资固定在名义利率上,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控制实际工资(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价值),从而影响就业率。[141]
到20世纪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些早期的名义工资合同模型感到不满,因为他们预测实际工资将是逆周期的(当经济下滑时,实际工资会上升),而实证证据显示实际工资往往独立于经济周期甚至略微顺周期。这些合同模式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也没有意义,因为不清楚企业为何会在长期合同导致低效率的情况下使用它们。新凯恩斯主义者没有寻找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商品市场以及由"菜单成本"价格变化模型导致的粘性价格。该术语指的是餐厅在想要更改价格时打印新菜单的实际成本;然而,经济学家也用它来指代与更改价格相关的更一般的费用,包括评估是否进行更改的费用。由于企业必须花钱来改变价格,他们并不总是将价格调整到市场完全清空的地步,这种缺乏价格调整的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可能处于失衡状态。使用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的研究证实,价格确实倾向于具有粘性。 商品的价格通常每四到六个月变化一次,如果不包括销售额,则每八到十一个月变化一次。[145]
虽然一些研究表明菜单成本太小,无法产生很大的总体影响,劳伦斯·鲍尔和戴维·罗默(1990)[u] 表明,实际的刚性可以与名义刚性相互作用,从而造成显著的不平衡。 真正的僵化发生在企业缓慢调整其实际价格以应对经济环境变化时。 例如,如果一家公司拥有市场力量,或者其投入成本和工资成本被合同锁定,它可能会面临真正的僵化。鲍尔和罗默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刚性使得企业的成本保持高位,这使得企业犹豫降价并损失收入。 由实际刚性造成的费用加上更改价格的菜单成本,使得公司不太可能将价格降至市场清算水平。[144]
协调失败
[编辑]
协调失败是经济衰退和失业的另一个潜在解释。在经济衰退期间,即使有人愿意在其中工作,也有人愿意购买工厂的生产,工厂仍然可以闲置。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衰退似乎是协调失败的结果: 无形之手无法协调通常最优的生产和消费流程。罗素·库珀和安德鲁·约翰(1988)[v]表达了一种通用的协调形式,作为具有多重均衡的模型,代理可以在其中协调以改善(或至少不损害)各自的情况。库珀和约翰的工作基于早期模型,包括彼得·戴蒙德(1982年)[w]的椰子模型,该模型展示了一个涉及搜索和匹配理论的协调失败案例。在戴蒙德的模型中,如果生产商看到其他人生产,他们更有可能进行生产。 潜在贸易伙伴的增加提高了某个生产商找到交易对象的可能性。 与其他协调失败的情况一样,戴蒙德模型具有多重均衡,一个代理的福利取决于其他代理的决策。戴蒙德的模型是一个"厚市场外部性"的例子,当更多的人和企业参与其中时,市场会运作得更好。其他潜在的协调失败来源包括自我实现的预言。 如果一家公司预计需求会下降,他们可能会减少招聘。 职位空缺的缺乏可能会让工人担忧,从而减少他们的消费。 这次需求的下降符合公司的预期,但完全归因于公司的自身行为。[152]
劳动力市场失败
[编辑]新凯恩斯主义者解释了劳动力市场未能清理的原因。 在瓦尔拉斯市场中,失业工人压低工资,直到对工人的需求满足供应。如果市场是瓦尔拉斯式的,失业者的数量将仅限于在工作中转换的工人以及因工资太低而无法吸引他们的工人。他们提出了几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可能会让愿意工作的工人失业。在这些理论中,新凯恩斯主义者特别与效率工资以及用于解释先前失业长期影响的内部外部模型相关,即短期内的失业增加变得永久化,并在长期内导致更高的失业率。[161]
自然科学-outsider模型
[编辑]经济学家对滞后现象产生了兴趣,因为失业率在1979年石油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中急剧上升,但没有回到之前被认为是自然率的较低水平。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劳伦斯·萨默斯(1986)[x]用内部外部模型解释了失业中的滞后现象,这些模型也由阿萨尔·林德贝克和丹尼斯·斯诺尔在一系列论文和随后出版的书中提出。[y] 内部人士,即已经在公司工作的员工,只关心自己的福祉。 他们宁愿保持高工资,也不愿减薪扩大就业。 失业的外来者在工资谈判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代表。 当失业率上升时,外来人员的数量也会增加。 即使经济已经复苏,外部人士仍然被排除在谈判过程之外。由经济收缩期产生的更大范围的外部人员池可能导致失业率持续上升。劳动力市场的滞后现象也提高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重要性。 如果经济的暂时性衰退可以导致长期失业率上升,那么稳定政策不仅提供暂时的缓解,还能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长期的失业率上升。[164]
效率工资
[编辑]
在效率工资模型中,工人的薪酬水平是最大化生产力而不是清空市场。例如,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可能会支付超过市场标准的费用,以确保员工能够负担足够的营养以实现生产。公司也可能支付更高的工资以增加忠诚度和士气,这可能带来更好的生产力。企业也可以支付高于市场工资以防止逃税。[167] 逃避现实的模式尤其具有影响力。卡尔·夏皮罗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84)[z] 创建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员工倾向于避免工作,除非公司能够监控员工的努力并威胁要解雇那些懒散的员工。如果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被解雇的逃课者就会简单地换一份新工作。个别公司支付给员工高于市场价格的溢价,以确保员工更愿意工作并保留当前的工作,而不是逃避责任,冒险换一份新工作。 由于每家公司支付的工资都超过了市场清算工资,因此合并后的劳动力市场未能得到清算。 这导致了一大批失业工人,并增加了被解雇的成本。 工人不仅面临工资下降的风险,他们还可能陷入失业者的困境。 将工资保持在市场清算水平以上会严重抑制逃避责任的动机,即使这会让一些愿意工作的工人失业,也能提高工人的效率。[169]
新增长理论
[编辑]更多信息: 内生增长理论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研究之后,直到1985年才进行了少量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保罗·罗默的论文[aa][ab]在激发生长研究的复兴方面特别有影响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蓬勃发展,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长期发展,并开始了包括内生增长在内的"新增长"理论。增长经济学家试图解释一些实证事实,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未能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东亚虎组织的繁荣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科技繁荣之前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下,增长率趋同已被预测,这一明显的预测失败激发了对内生增长的研究。[172]
三种新的增长模式家族挑战了新古典主义模型。第一个挑战了先前模型关于资本的经济效益会随时间减少的假设。 这些早期的新增长模式融入了资本积累的正面外部性,即一家公司在技术上的投资会因为知识的传播而为其他公司带来溢出效应。第二个重点在于创新在增长中的作用。 这些模型侧重于通过专利和其他激励措施来鼓励创新的必要性。第三组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复兴",它将外生增长理论中对资本的定义扩展到包括人力资本。这项研究始于曼昆、罗默和韦尔(1992年)[ac] which showed that 78% of the cross-country variance in growth could be explained by a Solow model augmented with human capital.[6],结果显示,78%的跨国增长差异可以用增强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来解释。[180]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国家可以通过一个鼓励其他国家技术与思想流入的开放社会实现快速的"追赶"增长。内生增长理论还建议,政府应该介入以鼓励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因为私营部门可能不会以最优水平进行投资。[181]
新的综合
[编辑]主条目: 新古典主义综合理论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综合"或"新古典综合",它融合了新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思想。[182] 从新古典学派出发,它采纳了红细胞假设,包括理性预期和方法;[183] 从新凯恩斯学派出发,它采用了名义刚性(价格粘性)[150]和其他市场不完善之处。新的综合理论表明,货币政策可以对经济产生稳定作用,这与新古典理论相反。新的综合理论被学术经济学家采纳,很快也被中央银行家等政策制定者采纳。[150]
在综合分析下,辩论已经变得不那么意识形态化(涉及基本方法论问题),而是更加实证化。 伍德福德描述了这一变化:[187]
有时对外人来说,宏观经济学家在经验方法论问题上似乎存在深刻分歧。 关于个别经验主张的可信度,仍然存在,并且可能永远都会存在激烈的分歧。 各种经验方法被用于数据特征描述和结构关系的估计,研究人员对特定方法的偏好各不相同,这通常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采用涉及更具体先验假设的方法。 但这样的辩论的存在不应掩盖在更基本的方法问题上达成的广泛共识。 无论是"校准主义者"还是贝叶斯估计的实践者,都认同进行"定量理论"的重要性,并且都认可纯粹数据特征描述与结构模型验证之间的区别。 并且两者对可以被视为结构的模型形式有着相似的理解。
伍德福德强调,现在数据特征化作品与结构模型之间有了更强的区别,后者不声称其结果与特定经济决策之间的关系,而结构模型则试图描述具有理论基础的实际关系和经济行为者所做的决策。 结构模型的验证现在要求其规格反映"家庭或企业面临的明确决策问题"。 伍德福德表示,数据特征分析在"建立结构模型应解释的事实"方面被证明是有用的,但不应作为政策分析的工具。 而是结构模型,通过代理人的实际决策来解释这些事实,构成了政策分析的基础。[187]
新的合成理论发展了称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红细胞模型,这些模型避免了卢卡斯批评。分布式发电模型提出了关于企业和家庭行为及偏好的假设;并计算了由此产生的分布式发电模型的数值解。这些模型还包括一个由经济冲击产生的"随机"元素。 在最初的红细胞模型中,这些冲击仅限于技术变革,但更近期的模型已经包含了其他实际的变化。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实际因素有时会影响经济。 弗兰克·斯梅茨和拉斐尔·沃尔特斯(2007年)[ad]的一篇论文指出,货币政策只能解释经济产出波动的一小部分。在新的综合模型中,冲击可以同时影响需求和供给。[185]
最近,新的综合模型的发展包括开发用于货币政策优化的异质代理模型:这些模型考察了在人群中拥有不同储蓄行为的消费者群体对货币政策通过经济传递的影响。[193]
2008年金融危机、大衰退与共识的演变
[编辑]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大衰退挑战了当时的短期宏观经济。很少有经济学家预测到这场危机,即使在那之后,对于如何应对它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新的综合理论形成于大缓和时期,并且尚未在严重的经济环境中进行测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危机源于经济泡沫,但综合分析中的两大宏观经济学派都没有太关注金融或资产泡沫理论。当时宏观经济理论未能解释这场危机,这促使宏观经济学家重新评估他们的思维方式。[197] 评论嘲笑了主流,并提出了重大重新评估。[198]
危机期间的特别批评针对的是在新综合分析之前和期间开发的分布式账本技术模型。 罗伯特·索洛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政府专家组的模型"对反衰退政策没有任何有用的见解,因为它在其本质上不可信的假设中构建了一个'结论',即宏观经济政策无能为力。"索洛还批评了分布式账本技术模型,该模型经常假设单一的、"代表性代理"可以代表构成现实世界的多种不同代理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罗伯特·戈登在1978年后批评了许多宏观经济学。 戈登呼吁更新不平衡理论和非平衡建模。 他贬低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已经明朗;他还呼吁更新经济模型,这些模型可以分别包括市场清算和粘性定价商品,如石油和住房。[201]
对分布式账本技术模型的信心危机并没有拆解新综合模型所体现的更深层次共识,[ae][7][187]以及能够解释新数据持续发展的模型。 那些曾受到更多公众和政治关注的领域,如收入不平等,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那些包含显著异质性的模型(与早期的通用数据分析模型不同)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里卡多·卡巴列罗在批评政府专家组模型的同时,认为金融领域的研究显示出进步,并建议现代宏观经济学需要重新定位,但不应在金融危机后被废除。2010年,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纳拉亚娜·科切拉科塔承认,通用电气模型对于分析2007年至2010年的金融危机"不是非常有用"。 但认为这些模型的适用性正在"提高",并声称宏观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达成共识,即通用数据仓库模型需要同时包含"价格黏性和金融市场摩擦"。尽管他批评了分布式账本技术建模,但他表示现代模型是有用的:
在21世纪初,...对于价格粘滞[af]的现代宏观模型而言,拟合问题消失了。 弗兰克·斯梅茨和拉夫·沃特斯使用新颖的贝叶斯估计方法证 明,一个足够丰富的新凯恩斯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欧洲数据。 他们的发现,连同其他经济学家的类似工作,导致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在全球中央银行的政策分析和预测中被广泛采用。[206]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查里在2010年表示,最先进的分布式发电模型允许行为和决策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这些因素包括年龄、先前经验和可用信息。[207] 在改进分布式账本技术建模的同时,工作还包括开发经济特定方面的异构代理模型,如货币政策传导。[193][202]
环境问题
[编辑]
从21世纪开始,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自然环境和健康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的益处)在经济学中得到了更广泛的研究。气候变化也被更广泛地认可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引发了关于经济学中可持续发展的辩论。 气候变化也已成为例如欧洲中央银行政策的一个因素。
生态经济学在21世纪也变得更加流行。在他们的宏观经济模型中,经济系统是环境的一个子系统。 在这个模型中,生态经济学中的收入循环流动图被一个更复杂的流程图所取代,该流程图反映了太阳能的输入,太阳能维持着自然输入和环境服务,并将其用作生产单位。 一旦消耗掉,天然投入物就会以污染和废物的形式从经济中排出。 环境提供服务和材料的潜力被称为"环境源功能",当资源被消耗或污染这些资源时,这一功能就会耗尽。 "汇功能"描述了环境吸收和传递无害废物及污染的能力:当废物输出超过汇功能的极限时,就会造成长期损害。[209]: 8
另一个生态经济学模型的例子是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思提出的甜甜圈模型。 这个宏观经济模型包括行星边界,比如气候变化。 这些来自生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模型虽然更受欢迎,但并未被主流经济思想完全接受。
异端理论
[编辑]主条目: 非主流经济学
非主流经济学家坚持那些足够脱离主流的理论,以至于被边缘化,并被建制派视为无关紧要。最初,包括琼·罗宾逊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合作,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非主流团体自我孤立,形成了孤立的群体。当今的非主流经济学经常在自己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不是主流期刊上,并且他们避免正式的建模,转而从事更抽象的理论工作。[210]
根据《经济学人》报道,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凸显了当时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和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当时的大众媒体讨论了后凯恩斯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这两种非主流传统对主流经济学影响不大。[215][216]
后凯恩斯经济学
[编辑]主条目: 后凯恩斯经济学
虽然新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思想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结合,后凯恩斯主义者则朝其他方向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者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综合理论,并认同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凯恩斯解释,该解释旨在发展没有古典元素的经济理论。后凯恩斯主义信仰的核心是拒绝古典和主流凯恩斯观点中的三个核心公理:货币的中立性、总替代性和遍历公理。[218][219] 后凯恩斯主义者不仅在短期内拒绝金钱的中立性,还将金钱视为长期的重要因素,而其他凯恩斯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放弃了这种观点。 总替代意味着商品是可以互换的。 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人们根据变化的比例调整他们的消费。遍历公理认为,可以根据过去和当前的市场条件来预测经济的未来。 没有遍历假设,智能体无法形成理性预期,从而削弱了新经典理论。在非弹性经济中,预测非常困难,决策受到不确定性的阻碍。 部分由于不确定性,后凯恩斯主义者在粘性价格和工资问题上的立场与新凯恩斯主义者不同。 他们不认为名义上的僵化是市场未能澄清的原因。 他们认为粘性价格和长期合同是稳定预期并缓解阻碍有效市场的不确定性。后凯恩斯经济政策强调需要减少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包括安全网和价格稳定。海曼·明斯基将后凯恩斯主义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概念应用于金融危机理论中,在这种理论中,投资者越来越多地承担债务,直到他们的回报无法再支付杠杆资产的利息,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明斯基的工作引起了主流关注。[214]
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
[编辑]主条目: 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

奥地利经济学派起源于卡尔·门格尔871年的《经济学原理》。 门格的追随者们形成了一群独立的经济学家,直到大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经济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区别基本上已经瓦解。 然而,奥地利的传统通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作品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一个独特的学派。 现代的奥地利人以其对早期奥地利作品的兴趣以及避免使用包括计量经济学在内的标准经验方法而著称。 奥地利人也关注市场过程而不是均衡。主流经济学家通常对其方法论持批评态度。[224][225]
哈耶克创立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该理论结合了门格尔的资本理论和米塞斯的货币与信贷理论。该理论提出了一种跨时期投资模型,其中生产计划先于最终产品的制造。 生产商调整生产计划以适应消费者偏好的变化。生产者回应的是"衍生需求",即对未来需求的估计,而不是当前的需求。 如果消费者减少支出,生产者认为消费者正在为以后的额外支出储蓄,从而使生产保持不变。结合可贷款资金市场(通过利率将储蓄和投资联系起来),这一资本生产理论导致了一个宏观经济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市场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偏好。哈耶克的模型表明,当廉价信贷引发资源错配的繁荣时,经济泡沫就开始了,导致生产早期阶段获得超出预期的资源,从而开始过度生产;而后期资本则没有资金用于维护以防止贬值。早期的过度生产不能通过后期维护不善的资本来处理。 当成品短缺导致"强制储蓄",因为可供销售的成品减少了时,繁荣就变成了萧条。[230]
注释
[编辑]- ^ Hicks, J. R.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April 1937, 5 (2): 147–159. JSTOR 1907242. doi:10.2307/1907242.
- ^ Modigliani, Franco.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 Money. Econometrica. January 1944, 1 (12): 45–88. JSTOR 1905567. doi:10.2307/1905567.
- ^ Solow, Robert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56, 70 (1): 65–94. JSTOR 1884513. doi:10.2307/1884513. hdl:10338.dmlcz/143862
 .
.
- ^ Swan, 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1956, 32 (2): 334–361. doi:10.1111/j.1475-4932.1956.tb00434.x.
- ^ Phillips, A. W.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November 1958, 25 (100): 283–299. JSTOR 2550759. doi:10.2307/2550759.
- ^ Clower, Robert W. The Keynesian Counter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Hahn, F. H., F.H.; Brechling, F. P.R. (编).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London: Macmillan. 1965.
- ^ Leijonhufvud, Axel.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 a study in monetary the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ISBN 978-0-19-500948-4.
- ^ Barro, Robert J.; Grossman, Herschel I. 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 61 (1): 82–93. JSTOR 1910543.
- ^ Leijonhufvud, Axel.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 a study in monetary the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ISBN 978-0-19-500948-4.
- ^ Malinvaud, Edmond.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considered. Yrjö Jahnsson lectures.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1977. ISBN 978-0-631-17350-2. LCCN 77367079. OCLC 3362102.
- ^ Friedman, Milto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 Restatement. Friedman, Milton (编).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 ^ Lucas, Robert E.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2, 4 (2): 103–123. CiteSeerX 10.1.1.592.6178
 . doi:10.1016/0022-0531(72)90142-1.
. doi:10.1016/0022-0531(72)90142-1.
- ^ Muth, John 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 Econometrica. 1961, 29 (3): 315–335. JSTOR 1909635. doi:10.2307/1909635.
- ^ Sargent, Thomas J.; Wallace, Neil. '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Optimal Monetary Instrument,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5, 83 (2): 241–54. JSTOR 1830921. S2CID 154301791. doi:10.1086/260321.
- ^ Hall, Robert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 (6): 971–987. JSTOR 1840393. S2CID 54528038. doi:10.1086/260724.
- ^ Lucas, Robert.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Brunner, K.; Meltzer, A. (编).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 New York: American Elsevier. 1976: 19–46. ISBN 978-0-444-11007-7.
- ^ Lucas, R.E.; Rapping, L.A. Real Wages,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 77 (5): 721–754. JSTOR 1829964. S2CID 154683563. doi:10.1086/259559.
- ^ Lucas, R. E.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 (3): 326–334. JSTOR 1914364.
- ^ Kydland, F. E.; Prescott, E. C.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 1982, 50 (6): 1345–1370. JSTOR 1913386. doi:10.2307/1913386.
- ^ Fischer, S. Long-Term Contract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85 (1): 191–205. S2CID 36811334. doi:10.1086/260551. hdl:1721.1/63894
 .
.
- ^ Ball, L.; Romer, D. Real Rigidities and the Non-Neutrality of Money (PDF).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0, 57 (2): 183–203. JSTOR 2297377. doi:10.2307/2297377.
- ^ Cooper, R.; John, A. Coordinating Coordination Failures in Keynesian Models (PDF).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 103 (3): 441–463 [11 July 2019]. JSTOR 1885539. doi:10.2307/1885539.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7 April 2019).
- ^ Diamond, Peter A.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in Search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2, 90 (5): 881–894. JSTOR 1837124. S2CID 53597292. doi:10.1086/261099. hdl:1721.1/66614
 .
.
- ^ Blanchard, O. J.; Summers, L. H. Hysteresis and the European Unemployment Problem.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86, 1: 15–78. JSTOR 3585159. doi:10.2307/3585159
 .
.
- ^ Lindbeck, Assar; Snower, Dennis. The insider-outsider theory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8. ISBN 978-0-262-62074-1.
- ^ Shapiro, C.; Stiglitz, J. E.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 (3): 433–444. JSTOR 1804018.
- ^ Romer, Paul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PDF).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 98 (5): S71–S102. JSTOR 2937632. S2CID 11190602. doi:10.1086/261725.
- ^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PDF).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 94 (5): 1002–1037. JSTOR 1833190. S2CID 6818002. doi:10.1086/261420.
- ^ Mankiw, N. Gregory; Romer, David; Weil, David N.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2, 107 (2): 407–437. CiteSeerX 10.1.1.335.6159
 . JSTOR 2118477. S2CID 1369978. doi:10.2307/2118477.
. JSTOR 2118477. S2CID 1369978. doi:10.2307/2118477.
- ^ Smets, Frank; Wouters, Rafael. Shocks and Frictions in US Business Cycles: A Bayesian DSGE Approach (PDF).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 (3): 586–606. S2CID 6352558. doi:10.1257/aer.97.3.586. hdl:10419/144322.
- ^ This consisting of: that macroeconomic analysis should use models with intertemporal and general-equilibrium foundations, that quantitative policy analysis should use econometrically validated structural models, that expectations should be modeled as endogenous, that real factors can cause shocks to both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at monetary policy is effective (as opposed to the view that it has no effects)
- ^ By the term "[statistical] fit", Kocherlakota is referring to the "model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that "were based on estimated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s, and so we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fit the existing data well." Kocherlakota (2010)
参考文献
[编辑]- ^ Blanchard 2000,第1377頁.
- ^ Dimand 2008.
- ^ Dimand 2008. : p.69.
- ^ McCallum 2008..
- ^ Mankiw 2006. : pp.37–38.
- ^ Klenow & Rodriguez-Clare 1997,第73頁.
- ^ Woodford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