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地那維亞的基督教化

畫面摘自丹麥坦德魯普教堂的祭壇畫,創作於12世紀。
北歐的基督教化,亦稱北歐的宗教轉變(古西諾斯語:Siðaskipti),是一個歷時甚久的宗教變革過程。在此過程中,北歐地區住民的信仰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基督教取代了原本的北歐多神教,成為主流信仰。
這場宗教轉變並非一蹴而就[1][2][3],而是一個歷時持久的過程。在此期間,北歐各地逐漸形成了中央集權的王國。那些最終建立王朝的家族,早在成為王室之前,就與已經信奉基督教的國家有著密切的聯繫。此外,許多北歐貴族與基督教國家的王公貴族有著親屬關係,尤其是波蘭、基輔羅斯(今天的烏克蘭)以及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一帶[4]。整場轉變大致在公元1300年前後才基本完成,彼時整個北歐社會才真正融入到基督教文化體系之中[5]。
北歐社會從多神信仰過渡到基督教信仰的過程,也是北歐地區社會、政治與文化發生深刻變革的時期[6]。原本散居的部落逐漸發展出國家,地方貴族成為國王,開始徵稅、鑄幣,並引入一神教信仰,以鞏固這種新興的國家體制[7][8]。
由於這一歷史時期的文獻資料普遍匱乏,學界往往參考冰島的歷史文獻來了解當時民眾對宗教變革的反應,儘管當時冰島聯邦的社會形態在許多方面與北歐大陸並不相同[9]。同時,後世修道院編撰的歷史記載(尤其是不萊梅的亞當所撰資料)往往帶有較強的目的性,因此研究中也有過度依賴這些資料的傾向。而另一方面,來自東歐的書面材料,如《往年紀事》以及拜占庭宗主教佛提烏一世的著作,則在學界研究中長期未被充分重視。
詞源
[編輯]古諾斯語「siðaskipti」(意為「風俗更替」)一詞由 siðr(意為「風俗」或「習慣」)構成,其意義接近現代所說的「文化」,但同時也涵蓋了傳統與宗教的內涵。丹麥學者普雷本·穆倫格拉特·瑟仁森認為,這個詞組的使用揭示了當時人們對這場宗教變遷的理解,表明當時人們將這一過程看作是從一個世界向另一個世界的轉變[10]。儘管在當時看來這場變化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一發展其實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起初,宗教轉變主要體現在外部形式上,比如更換了建築風格和儀式流程;真正的信仰轉變,即基督教的世界觀與神學理念的普及,是在較晚時期才逐步深入人心。隨著這種基督教思想的傳播,人們的道德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從而引發了生活方式與倫理規範的整體轉型[11]。
宗教轉變的趨勢與階段
[編輯]整個北歐宗教變遷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 斯堪地那維亞人開始接觸基督教。這種接觸發生的時間遠早於以往人們通常認為的傳教活動,也比那些被視為「首次接觸」的宣教之旅更早。但由於缺乏確切資料,具體時間難以確定。最早的接觸地點包括愛爾蘭、英格蘭、基輔和君士坦丁堡等地。率先了解一神教的,主要是上層社會人士和那些在海外活動的斯堪地那維亞人。
- 大批斯堪地那維亞人皈依基督教。這一階段大約始於9世紀中葉,尤其是在東歐的北歐移民定居點(如今的俄羅斯和烏克蘭一帶)以及拜占庭帝國的瓦蘭吉衛隊中。這些地區的早期北歐基督徒起初採用的是拜占庭希臘式的宗教儀式,後來逐漸轉向斯拉夫教會的禮儀傳統[12]。再後來,一些北歐人也參與了將拉丁禮儀傳入基輔的過程。
- 斯堪地那維亞納入拉丁基督教的教會行政體系。這一轉變大致發生在12世紀初期,標誌著北歐地區正式融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組織架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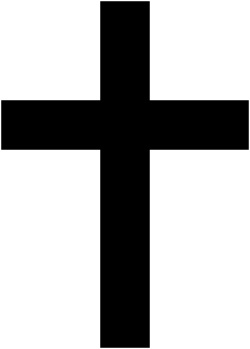
這一宗教轉變過程,是北歐社會在鐵器時代後期、維京時代及中世紀初期經歷的深刻社會、政治與文化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挪威宗教學者格羅·斯泰因斯蘭曾對此指出:宗教變革既是社會變化的重要推動力,同時也是深層社會變遷的結果[6]。在此之前,斯堪地那維亞地區普遍處於以地方貴族為核心的權力結構中,而在宗教變革過程中,政治權力逐步集中到三到四個主要王朝手中。
在有關這一時期的研究文獻中,對於宗教轉變的解釋視角和理論模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研究者對王權的看法——包括國王與教會的關係,以及在前基督教社會中王權的性質。通常情況下,基督教本身被視為一種積極的力量,基督教化則被看作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進程[8]。與此同時,對於這場宗教轉變的政治意義的解讀,也受到不同意識形態的影響。例如,持保守立場的學者往往對國王和教會持正面評價;而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學者則常帶有批判態度,反對教會和集權;至於自由主義的研究者,則更強調宗教轉變過程中的民主化傾向,以及農民社會在歷史進程中的推動作用[14] 。
過渡時期
[編輯]在宗教轉變發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信奉基督教與信奉舊有宗教的人群其實是混居在一起的,彼此之間的界限並不總是非常明確。因此,雖然北歐各國在名義上早在維京時代就已皈依基督教,但基督教信仰真正在民眾中扎根,實則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15]。例如,在丹麥國王藍牙哈拉爾正式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又過了將近一百年,才開始出現類似西歐那樣成體系的教會結構[16]。同時,直到13至14世紀,冰島民眾對傳統信仰的認知依然非常深厚,當地甚至還能創作出大量描寫古老宗教的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詩體埃達》和《散文埃達》等重要的北歐神話文獻,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得以保存至今。
基督教的思想和信仰是逐漸滲透進北歐社會的,並最終取代了原有的多神信仰體系。考古發現表明,在瑞典,這一轉變過程可能早在公元500年左右就已開始[17]。語言學研究也顯示,芬蘭語中有一大批與基督教相關的詞彙,是從早期的斯拉夫語中借入的。此外,丹麥早期的濕壁畫中也可以見到來自拜占庭藝術的影響[12]。歷史學家約翰·H·林德認為,有確鑿證據表明,芬蘭在瑞典十字軍到來之前,就已存在採用斯拉夫禮儀的基督教團體。他還指出,瓦良格人曾在這一過程中起到雙向橋梁的作用:早期的瓦良格人多皈依了拜占庭式或斯拉夫式的基督教,到了後期,又將拉丁教會的基督教傳播到了東歐地區。
應當指出的是,北歐在中世紀初期所接受的基督教,與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基督教形式有所不同。在當時的信仰觀中,耶穌常被描繪成一位征服者式的戰士國王[18]。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形象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反映出宗教觀念在整個轉型過程中的演變。
最早的宗教接觸
[編輯]
北歐人與基督徒之間的最早接觸,很可能發生在公元8世紀之前,甚至有可能早至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前。然而,直到9世紀20年代,基督教傳教士才在政治上獲得較為自由的空間,得以向北歐更大範圍的群體傳教[19]。考古學證據顯示,北歐大約從公元700年開始,才真正打開大門,與西歐建立起更為頻繁和深入的聯繫。這種聯繫主要通過貿易、掠奪和遠征等方式逐步加強。正是這種跨地域接觸的增多,為基督教在北歐扎根提供了重要條件[20]。

因此,宗教變遷的開端,正好與人們通常所說的「維京時代」同步。而關於「維京人」和「維京時代」的普遍印象,多半來自西歐各地修道院的記載。這些文獻構建了一種形象:維京人是一群與基督教世界發生過各種形式接觸的北歐人。換句話說,北歐出現在歷史記載中的時間點,往往就是他們與基督教文化首次相遇的階段。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今天所能讀到的關於北歐宗教的最早文字記載,很多是在基督教已在當地確立之後所寫成的。這些資料本身就深受基督教影響,也是在南歐和西歐文化影響不斷滲透北歐幾百年之後所產生的。因此,文獻中對北歐舊有信仰的描述,也常常是在基督教文化視角下進行的[21]。
9世紀初,教會在漢堡設立了一個總主教區,目的在於更有組織地推進北歐和東歐的基督教化進程,並記錄相關傳教活動。這些記載後來使得人們普遍認為,是南方來的傳教士使北歐皈依了基督教。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7],英格蘭教會以及烏克蘭的教會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並不亞於德意志地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改革的主動性在很大程度上其實來自北歐的國王們。例如,北歐最早的一批教堂,很多是依據英格蘭教會的傳統建造的,而以聖克萊孟命名的教堂則可追溯到基輔的傳統。據已知資料,北歐最早的教堂建於幾個主要的貿易中心——比爾卡、里伯和海澤比。這些城市在當時是北歐最重要的商業據點,經常有外國商人來往,其中包括不少基督徒。因此,這些教堂在最初的主要功能,並不是為了傳教,而是為了照顧和保護在當地活動的基督徒商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從一開始,教會中的神職人員就被允許向本地人傳教和施行洗禮[20]。
在9至10世紀之間,大批北歐人移居到他們祖先曾經洗劫過的西歐地區。最主要的定居地包括英格蘭西北部、愛爾蘭東部、蘇格蘭北部的沿海和島嶼,以及法國的諾曼第。這些地區在北歐人到來之前,基本已經是基督教化的社會。當這些人從維京海盜轉變為定居農民後,他們中的許多人也隨之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註 1]。通常來說,那些在基督教國家定居下來的北歐人,比那些後來返回本土的人更有可能長期保持基督徒身份。這樣一來,北歐人在西歐和東歐逐漸建立起多個基督教背景的定居點和殖民社區[19]。
從整個維京時代的一些墓葬中,考古學家發現了與基督教有關的遺物,例如鉛制十字架和蠟燭[22]。這類物品,以及墓葬習俗的變化,常常被用作判斷某地信仰轉變時間的重要線索。例如,在挪威西南部的考古發掘表明,該地區在10世紀上半葉就開始從火葬向土葬過渡。由於火葬從未被基督徒採用,而土葬在基督教傳入前也很少見,這種轉變通常被視為基督教信仰逐漸深入民間的標誌。相比之下,丹麥的這一轉變則大致發生在10世紀中葉。至於挪威的內陸地區以及特隆赫姆周邊,則較長時間內仍以傳統信仰為主,未完全基督教化[23]。
君王的皈依
[編輯]
來源:Jürgen Howaldt
當丹麥國王藍牙哈拉爾於公元960年代皈依基督教時,他的許多臣民或許早已成為基督徒[24],但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堅守著傳統信仰。類似的情形同樣出現在其他北歐國家:一旦君主改宗,新宗教的確立便具有象徵性的國家意義。然而,這種「國家基督教化」的狀態在之後的多年間都只是形式上的。即便藍牙哈拉爾正式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他依然不得不容忍某些封臣保留異教信仰。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異教貴族,是挪威的哈康·西居爾松伯爵[1]。到了10世紀最後的四十年間,幾乎整個北歐在名義上都已成為基督教國家。唯一的重要例外是瑞典的斯韋阿蘭(今瑞典中部),儘管梅拉倫地區已擁有龐大的基督徒群體,斯韋阿蘭的官方宗教祭祀仍為異教。真正的宗教轉變直至公元1080年代才在此地實現。
促使北歐諸王皈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世紀早期北歐社會結構日益複雜與組織化的發展。這一社會轉型對宗教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基督教相較於傳統信仰,更具備滿足這些要求的能力[25]。君權的集中化與官僚體制的建立,正是強化王權的關鍵工具,而當時,只有教會才能提供這套成熟的行政框架[26]。因此,在中世紀前期歐洲新興國家的誕生過程中,國家統一與基督教化之間常常是同步發生的。在10世紀,首先接受新信仰的主要是貴族與王室圈層,而大眾的信仰轉變則較為緩慢。這一宗教更替的過程持續了幾個世紀,直到舊信仰才逐漸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在公元1100年前後,北歐教會制度的基礎逐漸確立。丹麥的第一批主教早在10世紀中葉就已被任命,但這些主教對其教區所命名的城市多半只有名義上的聯繫,甚至可能從未親臨其任教的教區城市[27]。到了克努特大帝統治時期,丹麥開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教區系統。至1060年左右,丹麥八大教區的疆界已基本確立,並保持至宗教改革時期[28]。直到1103年,隨著隆德設立第一位大主教,北歐才正式成為獨立的教會省份。在此之前,儘管漢堡-不萊梅大主教區宣稱對整個北歐教會省擁有管轄權,但北歐地區實際上一直處於事實上的自治狀態,未真正納入教皇體制之下。
教會的鞏固
[編輯]
在11世紀的北歐,神職人員通常仍然具有外國背景。直至11至12世紀之交,基督教在丹麥的制度化程度才足以支撐本地牧師的培養,而在其他北歐地區,這一進程甚至開始得更晚[29]。在12世紀之前建造的教堂,通常規模都較為簡陋。它們大多設有一個講壇或高座,專供出資興建教堂的地方貴族及其家族使用,而神職人員及僕役則席地而坐,周邊的農民群眾則完全缺席於禮拜活動之外[5]。在基督教傳入之前,廟宇與聖所的管理職能多由地方領主或世族家主承擔。當他們改宗為基督徒之後,這一角色便轉為資助教會的宗教贊助人[30]。彼時,幾乎所有教堂均為木結構建築,因為石造建築在當時的北歐仍屬罕見。北歐早期教堂的建築風格亦呈現出完全矩形的簡約形制,與西歐常見的三廊式巴西利卡結構大相逕庭[31]。最早期的木製教堂如今已無一保存,大多數在12至13世紀被更大的石砌教堂所取代——但挪威是一個例外,在那裡,木構教堂的建造傳統被延續並高度發展,成為歐洲建築史中的一項獨特現象[32]。
到了12世紀,修道院的建立,尤其是熙篤會的傳入,極大地推動了教會對廣大平民的開放。彼時的西歐已經興起一種全新的基督教形式,強調個人信仰、洗禮的意義與心靈的皈依。這一宗教改革的思想迅速傳入北歐[5]。其具體體現之一,是在原本無教堂的地區新建教堂,以及對既有教堂的擴建,以確保普通民眾也能參與彌撒和禮拜。從公元1100年起,這種教堂擴建運動在整個歐洲均有體現,包括北歐地區[33]。丹麥至今仍保留著一批源自該時期的教堂建築。自11世紀下半葉起,北歐開始興建中歐式樣的石砌巴西利卡,這些教堂主要為主教座堂。早期的這些高水平石教堂建設,大量依賴於來自國外的建築師和工匠。直到磚石建築技術普及之後,才逐漸形成本地的建築專業人才群體[34]。宗教轉變所帶來的這場文化革命,在教會制度於公元1300年前後全面確立後,才算達到高潮。不過,即便到了這一時期,北歐的基督教仍未完全擺脫某些前基督教元素的影響[35]。
與此同時,宗教轉型也對性別角色在宗教實踐中的地位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皈依基督教之前的時代,曾存在一種名為「gydje」的女性宗教職能者,後世文獻將其視為一種「女祭司」角色。她們在與生育崇拜、弗雷祭儀相關的儀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可能也參與了狄斯祭與精靈祭等信仰活動。雖然 gydje 的身份不如男性神職者 goden 權力顯赫,但她們依舊享有較高的社會聲望。然而,隨著基督教的傳播,這一女性宗教角色逐漸被徹底抹除,因為在基督教體制下,並未為女性保留任何等同地位的神職職能[36]。
宣教中心與傳教實踐
[編輯]在公元6至7世紀間,英格蘭曾是一個基督教文化極為繁榮的中心,其影響力波及整個西歐。許多來自不列顛群島的神職人員在這一時期以傳教士身份踏上歐陸,即使是前往一些已名義上皈依基督教的地區。這類傳教士在當時常被稱作「朝聖者」(pilgrimme),原意即「旅人」或「異鄉人」。他們的旅行背後,蘊含著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中的一個核心觀念:自願放逐。這种放逐被看作一種極致的苦行方式,具體表現為修士們長途跋涉至異邦他地,以宣講基督信仰。據記載,最早進入北歐傳教的基督徒是英格蘭人威利布羅德,但極有可能還有其他英國傳教士亦曾活動於此[37]。我們今天能夠從語言史上追蹤早期北歐教會所受的英格蘭影響:例如「教堂」(kirke)、「聖杯」(kalk)、「薰香」(røgelse)等核心禮儀用語,皆可溯源至古英語[38]。
從現存文獻來看,漢堡-不萊梅大主教區常被視為北歐基督教化的主要起點。但這種印象很大程度上源自主要由該主教區編纂人員所撰寫的史料,他們在記錄中幾乎忽略了來自英格蘭或愛爾蘭的傳教活動。然而,北歐人與基督教的接觸,其實早在9世紀德國傳教正式展開之前便已開始。例如,那些曾作為人質、外交使節或僱傭兵進入基督教國家宮廷的北歐人,常受到基督教文化的薰陶。不過,這類影響主要限於社會上層[19]。另一條重要的傳教途徑,是通過大量遷往不列顛群島的斯堪地那維亞移民。自公元870年代起,這些定居於英倫的北歐人中,已有不少迅速皈依了基督教[39]。至10世紀,英格蘭教會中已有許多神職人員出身於英丹混血背景,其中甚至包括三位大主教。據認為,他們對在北歐進行福音傳布持有高度熱忱[19]。考古學發現亦證實,尤其在丹麥與挪威,存在大量反映英格蘭影響的物證。此外,在12世紀初期,北歐地區仍在興建英式教堂建築[34]。1022年,羅斯基勒主教由坎特伯雷大主教親自祝聖,反映出丹麥國王克努特大帝試圖使丹麥教會脫離漢堡-不萊梅的控制、轉而歸屬英格蘭教會。不過,這一努力不久便因政治壓力而中止,丹麥被迫再次接受漢堡-不萊梅對整個北歐教會省的宗主權[40]。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和芬蘭的情況與丹麥不同,在這兩個地區,直至11至12世紀,仍能觀察到來自東方宗教的顯著影響[41]。
傳教士在北歐的活動,往往高度依賴地方豪族的資助與庇護。他們通常隨領主或國王一起巡遊各地[27],在權貴莊園中落腳[5]。而隨著時間推移,傳教士們逐漸建立起一個與本土宗教系統相抗衡的平行宗教網絡[42]。當最早的修道院在北歐落成時,它們便成為傳教活動與基督教制度化建設的重要基地,而這些修道院多由國王或大領主倡建,有些甚至可能在極早期階段就已建成[43]。
從有關傳教行動的記載中,我們可以勾勒出當時基督教統治者在異教領地推行信仰的基本策略。通常由一位高級神職人員(如主教)率隊,組成一支使團,首要任務是拜訪當地統治者以博取其興趣和支持,之後方能展開進一步傳教。這些使團常常將當地的男童帶回基督教國家加以培養,使其將來再度作為傳教士返回故土。另一種策略則是通過展示基督教上帝的「力量」來削弱本土信仰,這可能通過直接動武或摧毀異教聖地來實現[37]。通常來說,異教社會最初會容忍基督徒的存在,但一旦基督徒褻瀆或摧毀聖所,衝突便迅速爆發。因為傳統觀念允許宗教信仰多樣性,但也要求對神聖空間的尊重[9]。
中世紀早期的北歐基督教
[編輯]
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並非一個統一規範的宗教體系,而是在歐洲各地呈現出顯著的地方差異。儘管整個基督教傳播區域存在某些核心教義的一致性,但各地的宗教實踐卻因地制宜,迥然有別。例如,在北歐地區,基督教神職人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未被要求守獨身[44],這一教規直到中世紀盛期才逐步推行。此外,不同地區所遵循的宗教規範與禮儀制度,也展現出極大差異。傳入北歐的基督教,在形式上呈現出一種更具戰鬥性的特徵,這一點不但有別於同期盛行於南歐的溫和基督教模式,也與當代人們所熟知的基督信仰大相逕庭。在日耳曼語族文化所接納的基督教中,耶穌常被描繪為一位凱旋的戰王,正在與邪惡勢力進行一場無盡的戰爭。這種形象很明顯是對舊宗教中雷神托爾角色的繼承與轉化[45]——托爾作為神祇中最具戰鬥精神的一位,在民間信仰中具有極高地位。隨著基督教在北歐的制度化進程不斷推進,它也逐漸吸收了本地文化的特色。例如,教宗額我略七世在1080年致丹麥國王哈拉爾三世的一封信中抱怨說,當地的神職人員竟要為天氣變化負責,這顯然是源於異教時代的自然信仰殘餘,即將祭司視為能與自然溝通、左右風雲之人[46]。北歐基督教制度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其宗教機構無法獨立於其施主存在。教會的存在往往仰賴某位權貴的保護與資助,這使得基督宗教在北歐更接近於一種「功能體」而非「自治機構」。這一點與前羅馬帝國地區的基督教形成鮮明對比——在那裡,教會逐漸演化為一套自給自足、獨立運作的制度體系[47]。
儘管如此,某些教會制度在整個基督教世界中具有普遍的重要性,其中之一便是主教制度。主教在宗教儀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因為在當時,普通神父僅能執行少數幾種禮儀,而教堂的祝聖以及神職人員的任命則必須由主教親自進行[48]。人們如今所熟知的強大教宗權威與中央集權的天主教會,其實是1074年敘任權鬥爭之後的產物;而在此之前,這一結構尚未形成。因此,維京時代建立於北歐的教會組織,與後來成熟的天主教體制大不相同。在這一時期,教區的實際控制權掌握在國王與大貴族手中,由他們任命地方教職人員。這種制度與日耳曼傳統的異教結構高度一致:在舊信仰體系中,神廟或祭壇歸地方豪強所有,建於其私有領地之上。基督教會的初期發展,在北歐仍遵循這一模式——新建教堂屬於其出資人,由他出面管理教務與運營[47]。因此,中世紀早期的神職人員並未受到統一的教會權威結構的規範管理[49]。這也導致地方教會在形式、功能與神學立場上存在顯著差異,呈現出強烈的地方性與自主性。特別是在日耳曼地區,早期教會經常相對獨立於羅馬體系而運行[47]。
基督教的部分內容與北歐舊宗教有直接對應關係,而另一些內容則顯得極其陌生難懂。基督教的永恆輪迴,包括「死亡與復活」的核心主題,對於當時的北歐人而言並非完全陌生;因為這一概念與他們自身神話傳統中有關宇宙更替與生命輪迴的觀念多有呼應。如北歐神話中的諸神黃昏與新世界的重建,即體現出對毀滅之後再生的認知。類似地,諸如守護天使、神意指引,以及即將到來的末日審判等觀念,也可在北歐本土神話中找到對應[30]。然而,也有一些基督教的核心概念與北歐世界觀徹底不兼容,譬如耶穌被視為神人與人之間的代贖者,通過自我犧牲承擔人類原罪的「苦難史」,這一點在北歐傳統中毫無先例。在前基督教時代的北歐,諸神的職責乃是保障集體福祉,提供所謂的「和平與豐年」,這是對社會整體的護佑。而基督宗教則將重心移至個人的信仰與救贖,強調人與神之間的私密聯繫。這一轉變構成了深層的信仰斷裂。此外,基督教的排他性亦是與北歐舊宗教體系截然不同的重要方面。在基督教的宇宙觀中,只有對耶和華的信仰才是通向救贖的唯一正道,其他信仰體系則被一概視為邪惡的化身或誤入歧途的信仰[50]。相較而言,北歐的傳統信仰具有更高的包容性,它不否定他者宗教的存在,只要求在社會禮儀和神聖秩序中予以尊重[51]。這種「共存型」世界觀,與基督教所推崇的獨尊主義存在根本分歧。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正是基督教在解釋「生命意義」與「人類存在目的」方面的系統性回答,構成了它在思想層面壓倒北歐傳統宗教的重要優勢。相比之下,傳統北歐神話雖具備豐富的象徵結構與敘事模式,卻缺乏對人類本體意義與終極命運的系統詮釋能力[52]。
皈依基督教不僅僅意味著接受一套新的神話觀,更意味著服從教會的儀式規範與倫理體系[44]。而這種皈依行為,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遠非形式主義的表演,他們通常真誠地相信神力在世間具象化地顯現。彼時,抽象、超驗、不介入人世的神明觀念尚未在大眾中普及。因此,對於個體而言,信仰的轉換是深刻而真實的精神選擇,基督信仰帶來的宇宙解釋力與內在秩序感,確實能夠賦予人們更強烈的認同感。這一邏輯同樣適用於當時的君王階層,他們的改宗並非單純的政治策略,更可能是一種出自心理契合與信仰需要的深度認同[5]。
過渡時期的異教信仰
[編輯]在基督教傳入之際,日耳曼文化中的社會結構與宗教觀念,在多個方面都與基督教所植根的羅馬傳統存在顯著差異。日耳曼諸王國的政治體制遠較羅馬帝國為分散。在傳統觀念中,日耳曼國王的職責主要在於維護與神靈之間的良好關係,即確保「和平與豐收」(fred og år),以及在戰時擔任軍事首領。國家的政治權力則主要集中於各地擁有大片土地的貴族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在實質上擁有高度自治權,與國王之間的聯繫,僅通過忠誠誓言維繫。與後來的羅馬體制不同,在日耳曼世界中,國王並不擁有全部領土的所有權;每一塊土地都屬於私人財產。這種制度下,獨立於個人之外的機構所有制形式(如羅馬法下的公法人制度)是根本不存在的。法律上,任何形式的組織都無法在脫離特定個人的前提下獨立存在[53]。也正是這一點,構成了前基督教信仰在面對基督宗教時的主要劣勢:它缺乏統一的組織結構、集中權威與普世性的教義體系。相反,前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呈現出強烈的地方性與個體性,這使得基督教更容易逐步滲透進社會各階層與制度之中,最終占據主導地位[54]。
在傳統的北歐社會中,宗教不僅是個人信仰的問題,更是社會凝聚力與身份認同的核心[9]。神廟與祭祀場所的日常管理,多由地方最有權勢的家族負責,其家族首領往往也同時擔任祭司的角色。正因如此,當一位酋長或領主皈依基督教時,這一決定通常也意味著整個社區隨之改信[30]。
北歐地區之所以經歷了漫長的宗教過渡期,其最顯著的證據之一便是:大量源自舊信仰的元素長期存續於民間傳說與習俗中,甚至延續至近代。在這一轉型期內,異教信仰本身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與基督教接觸的日益頻繁,原有的儀式與信仰體系勢必遭受影響,許多觀念經歷了重構。例如,「瓦爾哈拉」這一對戰死者來世的理想描繪,很可能是在公元10世紀中葉,在基督教「天堂」觀念的影響下形成的[55]。這場文化變革也促使拉丁文學傳統在北歐傳播,帶來了兩項深遠影響:一方面,原始的北歐信仰終於被文獻記錄下來;另一方面,關於舊信仰的記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基督教與拉丁文化的詮釋框架所塑形[8]。例如丹麥史學家撒克遜文人薩克索·格拉瑪提庫斯在記述北歐遠古文化時,便將其描述為「未開化」與「野蠻」的歷史階段,是對後來的基督教文明的一個不完美前奏[56]。而冰島史詩作者斯諾里·斯圖魯松則嘗試以古典文學的結構方式,較為中立地書寫這些傳統神話。
即便在名義上完成了宗教轉變後,舊有的宗教傳統依舊對人們產生著深遠影響。畢竟,它們在集體記憶中長期承擔著賦予世界秩序與保護功能的角色。然而,這些信仰體系也逐步面臨來自新教義的挑戰,例如「原罪論」與「三位一體」觀念[15]。考古學研究亦提供了有力的實證。例如在斯德哥爾摩附近的洛沃恩墓地的發掘顯示,當地的異教喪葬習俗延續時間之久,至少跨越了150至200年[57]。而這一地區,即便在當時,也處於權力核心地帶,說明異教傳統在社會上層亦未能迅速消退。另一個例證來自於13世紀挪威的貿易中心卑爾根,在以盧恩字母為代表的出土文物中,仍可見對女武神等北歐神祇的祈禱,而基督教概念則幾乎完全缺席[58]。這表明,舊信仰在民間層面擁有極強的生命力,並未因官方的改宗而立即消亡。
共存、衝突與宗教融合
[編輯]到公元9世紀中葉,基督教在丹麥與斯韋阿蘭已獲得一定程度的寬容。在三座主要城市中已有教堂設立,神職人員獲准公開講道與施行洗禮[19]。然而,從9世紀至13世紀的文獻資料來看,基督教與本土宗教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和平共處[59]。雖然9至10世紀這段時期大體呈現出一種宗教寬容的氛圍,但此種狀態隨後被新一階段所取代——在這一階段中,異教信仰開始遭受有組織的打壓與取締,而基督教則確立為唯一合法宗教。此一轉變的前提,是建立起具備制度化架構的教會組織,並且獲得強大政治力量的支持,尤其是王室的鼎力相助[1]。
在前基督教時代,其他信仰並非出於某種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寬容」而被接受,而是因為這些信仰本就存在於現實之中,人們不得不予以應對與承認[9]。因此,在這種多神論的世界觀中,接納一位新神祇,並不意味著要排斥既有神明。在這種觀念下,人們甚至可能將耶穌作為另一位神明,與奧丁、索爾等舊神並列崇拜。這種包容性的思維方式,很可能是造成基督教傳播過程漫長而漸進的重要原因之一[30]。隨著基督宗教逐步發展為與本土信仰相對立的體系,在某些情境下,為避免激烈衝突,社會不得不採取務實性策略進行調和與過渡[60]。
在早期傳播階段,基督教極有可能僅被視作對舊信仰的補充。若干史料也記載了一些情形,其中基督教神靈與北歐諸神被一併提及,地位並無明顯高下之分,反映出宗教融合的現象在過渡時期相當普遍[61]。

來源:Hamish Laird
宗教衝突
[編輯]新舊宗教的衝突並非僅發生在國家或部族層面,在家庭內部也常常引發劇烈矛盾。例如在《格陵蘭人的薩迦》中記載,紅鬍子埃里克的妻子西約德希爾德(Þjódhild)在皈依基督教之後,便堅決拒絕與依舊崇拜舊神的丈夫同居[62]。由此可見,即使在最私密的領域,宗教差異亦可能帶來實際分裂。
宗教之所以能夠引發廣泛衝突,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宗教從來不是一種純粹的私人信仰事務,而是在多重層面上影響整個共同體的結構與秩序。國王作為國家的宗教首腦,其最重要的職責之一,便是維持與神靈的良好關係。若他未能完成此項任務,則整整一個社會都有可能因此而遭遇災難。因此,當國王改宗之時,常常被視為威脅社會安定的舉動,並引發抗議或內亂。另一個頻繁產生衝突的領域,是舊有宗教實踐的被禁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基督教會對於祖先崇拜的明令禁止。然而,祖先崇拜原本是前基督教宗教體系中的一個根本支柱,被廣泛認為是維護宗族秩序與精神聯繫的關鍵儀式。因此,此類禁令往往直接觸及社會與文化的核心,引發了深層次的對抗[63]。
宗教融合
[編輯]在文字記載中,幾乎沒有明確證據表明北歐在宗教轉型時期曾廣泛存在有意識的宗教融合現象。相反,更常見的是兩個彼此並存的信仰體系:即使在早期階段,耶穌往往也只是被視為「眾神中的一位」[62]。然而,大量實物遺存卻揭示出這兩種宗教之間的符號混合現象——例如,一些文物上同時出現了基督教與異教的符號圖騰。然而,僅憑這些個別實例,難以準確界定這種混合背後究竟反映了何種宗教或社會現實:這可能是真實融合性信仰的殘餘;也可能源於人們對宗教象徵內涵的模糊理解;或是一種宗教上的雙重保險策略;甚至可能僅是將符號從原有語境中抽離所致[64]。更重要的是,這些現象並非只出現在短暫的過渡期中,而是在13世紀仍有跡可循,例如丹麥曲半島的格特魯普教堂中,洗禮石上雕刻著托爾(雷神)之錘的圖案[65]。
總體來看,有充分理由推測,北歐人確實保留了大量舊有關於神明職能的觀念,只不過將這些觀念轉嫁到了基督教的上帝身上。例如,在許多情況下,北歐基督教中上帝仍被視為維繫社會秩序與物質豐裕的保障者,這一點顯然延續了舊有神明的職能。類似地,傳統的大型年度節慶雖然改換了形式,但在基督教節期中仍然得以延續,且與異教時代一樣,每個人都有義務參與。其他宗教儀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前宗教的基本結構。更有甚者,某些異教儀式甚至被直接納入基督教的框架之中——雖然教會主流往往將這些行為視為「迷信」或「異端」[44]。因此,到11世紀時,北歐的基督教信仰體系尚未徹底脫離舊有體系的影響[66]。
在其他層面也能清晰觀察到延續性。例如,許多古老的異教祭祀中心在改宗之後繼續被用作宗教聖地,只不過轉換為了基督教的形式。像維堡、歐登塞以及烏普薩拉等地後來都設立了主教座堂[44]。這類現象表明,地理空間的神聖性得以保留,只是符號體系被替換了。此外,還有一些異教紀念性建築被有意重新定義,賦予基督教意義。例如,丹麥第一位基督教國王藍牙哈拉爾對耶靈異教遺址所做的改建:他在一座古老石圈與兩座墓冢之間修建了一座非比尋常的大型基督教堂。與此同時,他將其父親——異教王老戈姆的遺體從舊墓中遷出,並安葬於新教堂內。而在原墓中,則放置了如蠟燭與銀杯等基督教聖物,似乎意在通過儀式方式,將這一原屬異教的空間納入基督教神聖領域之中[67]。
矛盾的是,在這場從傳統異教向基督宗教轉型的漫長過程中,兩種信仰體系之間並不存在某種不可逾越的深淵。例如,基督教中的聖徒往往被視為通向多神宇宙觀的媒介,這基本上是一種有意識的宗教融合策略[35]。
但新舊宗教間的影響也並非純然單向,基督教反過來亦對北歐神話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文字記載的神話體系中,多個角色可能已受到基督教觀念的塑造。例如,巴德爾這個人物常被解讀為耶穌在本土神話中的變體,而海姆達爾所吹響的加拉爾號角在諸神黃昏中宣告末日的來臨,常被視為與《聖經》中加百列天使號角的功能相對照[22]。這種影響極可能早在羅馬或日耳曼鐵器時代便已開始。因此,我們今日面對的北歐神話與宗教體系,已很難準確區分出哪些元素為原生的、本土的,哪些則是受基督教的深層影響之後的產物[29]。
宗教與政治
[編輯]
在歐洲中世紀早期新興的各個國家中,王國的建立與基督教化過程之間關係密切[26]。同樣地,北歐中央王權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確立,也與從異教向基督宗教的轉變高度同步[8]。這一現象部分是因為基督教會能夠為諸侯提供一整套意識形態框架,以支撐其新生的國家機器[68]。同時,法蘭克王國的皇帝也意識到,將其東部和北部強大的異教鄰國轉化為基督教徒,不僅有助於宗教傳播,也能提升王國的安全,進而把這些鄰國納入其附庸體系[69]。查理曼大帝通過武力征服撒克遜人,並強制其改宗,使得法蘭克王國直接與丹麥接壤。這一變化使得丹麥也面臨同樣遭遇的風險。因此,蘭斯的埃博和不萊梅的安斯加爾當時能夠發起傳教嘗試,顯然與這種背景密切相關[20]。
9世紀後半期,維京人對西歐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掠襲行動,而法蘭克王國的國力也顯著衰退。在這一時期,沒有關於傳教士前往北歐的記錄,原因可能是當地首領認為,在基督教國家衰弱的情況下,支持教會已無必要,基督教也因此被視為一種軟弱的宗教。到了10世紀初,基督教國家在防禦維京襲擊方面變得更為有效,並開始主動向丹麥發動進攻。在這樣的局勢下,基督教傳教活動重新獲得支持,因為丹麥國王此時更需要與基督教國家維持良好關係[70]。丹麥國王能在965年皈依基督教,也與當時國內已經存在一定規模的親基督教群體有關,這一群體為國王的宗教轉變提供了必要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國王的皈依並非個人決定。在傳統觀念中,國王是國家宗教事務的重要代表,因此在改變信仰之前,必須確保獲得國內貴族階層的廣泛支持[1]。
對一般的北歐人來說,在前往基督教地區旅行時,若能表現出與基督教的關聯,不僅可以帶來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好處,也有助於擺脫「外來者」的身份,從而與當地人建立更良好的關係[71]。
北歐各地的基督教化歷程
[編輯]丹麥的基督教化
[編輯]
最早有記載的在今丹麥地區進行的基督教傳教嘗試,是由被稱為「弗里斯蘭人的使徒」的威利布羅德發起的。他曾在公元710年至718年間前往什勒斯維希地區傳教,並拜訪了當時的丹麥國王阿甘提爾(拉丁文記作Ogendus)。據記載,這位國王「野性如獸,冷硬如石」,說明威利布羅德和隨行傳教士的努力收效甚微[72]。雖然國王對他們表示禮遇,但對改信基督教並無興趣。不過,阿甘提爾允許他帶走三十名年輕人前往弗里斯蘭,接受教育,以便日後繼續向「野蠻的丹麥人」傳播福音[73]。此後的一百多年間,沒有更多關於傳教的記載。直到公元823年,蘭斯大主教埃博與後來的不萊梅主教維勒里希訪問丹麥,期間為一些丹麥人施行洗禮,基督教傳教活動才再次出現。埃博後來又兩次返回丹麥,試圖擴大改信人數,但史料並未說明他是否取得進一步成果[73]。
不久後的826年,日德蘭國王哈拉爾·克拉克被霍里克一世驅逐,被迫流亡。他向法蘭克皇帝虔誠者路易尋求支持。皇帝答應為其提供援助,並將弗里斯蘭公國作為封地賜予他,條件是哈拉爾必須放棄舊神,接受基督教洗禮。哈拉爾遂與妻子、家人及約400名隨行的丹麥人一起,在英格爾海姆受洗[74]。當他返回日德蘭試圖重奪王位時,應皇帝要求,修士安斯加爾隨行一同前往。然而,哈拉爾再次被霍里克驅逐,安斯加爾在丹麥失去支持後,決定將傳教目標轉向瑞典。831年,漢堡大主教區成立,安斯加爾成為首任大主教。該教區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負責向北歐地區傳教[75]。
845年,霍里克領導丹麥軍隊襲擊並洗劫漢堡,安斯加爾被迫逃往不萊梅,並在那裡重建教區[75]。不過,安斯加爾後來重新獲得了霍里克的信任。860年,霍里克允許他在海澤比建立教堂,這是丹麥境內最早的基督教教堂。幾年後,另一座教堂在里伯建成。948年,里伯成為北歐地區最早設立的主教教區,隸屬於漢堡-不萊梅大主教區。根據傳統記載,該教區的首任主教聖利奧夫達格在一次渡過里伯河時遇害[76]。
瑞典的基督教化
[編輯]

正如前文所述,最早有記錄的基督教傳入瑞典的嘗試,是由安斯加爾於公元830年發起的。當時他受瑞典國王造墳者比約恩邀請,獲准在比爾卡建立教堂。然而,安斯加爾的傳教工作並未引起當地人的廣泛興趣。大約一個世紀後,漢堡-不萊梅大主教烏尼再度嘗試傳教,但同樣未見顯著成效。在10世紀,多位英格蘭傳教士曾活躍於西約特蘭一帶進行布道。
瑞典首位皈依基督教的國王是奧洛夫·舍特科農,他於990年代登上王位。然而,基督教與舊有的異教信仰在瑞典長期並存,直到11世紀末才正式結束這一局面。在這一時期,異教徒與基督徒之間達成某種程度的宗教容忍與共處[77]。不萊梅的亞當在其歷史著作中提到,11世紀時烏普薩拉仍有一座活躍的異教神廟[78]。儘管目前尚未發現確鑿的考古證據,但現代教堂下方曾發現一處木結構遺蹟,可能與該神廟有關;也有學者認為,它可能是更早時期基督教堂的遺址[77]。
關於這一時期的瑞典史料極為有限,但一些傳說文學記載了基督徒與異教徒之間的暴力衝突。《奧克尼薩迦》與《赫爾薇爾薩迦》都提到,1080年代,瑞典國王老英格決定終止烏普薩拉異教神廟的活動,引發了民眾強烈反對,最終被迫流亡。隨後,其妹夫布洛特-斯文被選為國王,條件是必須繼續保留異教信仰和儀式。但三年後,老英格秘密返回,率兵包圍斯文的大廳並縱火焚燒,廳內人員或被活活燒死,或在逃出時被殺。此後,神廟應該已被徹底摧毀[79]。1164年,烏普薩拉被設為大主教區,標誌著基督教會在瑞典的制度性確立。
瑞典的異教與基督教之所以能相對和平地共存至11世紀末期,主要是因為新宗教在民眾中逐步獲得認同的同時,舊信仰仍被視為法律與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是新近皈依者也不例外[80]。為了維持統治,老英格必須爭取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其中也包括異教徒。這種忠誠曾在挪威國王馬格努斯三世入侵西約特蘭時受到考驗。老英格據稱成功動員了3,600人的全體雷當軍隊,並擊敗了入侵者[81]。正因為這一時期瑞典仍保持宗教寬容,在丹麥和挪威已正式皈依基督教後,瑞典在北歐其他地區仍被視為「異教國家」。即使在12世紀,瑞典名義上已全面基督教化,挪威國王西居爾一世仍以「傳教」為名出兵斯莫蘭,宣稱要使當地人「皈依基督教」。
耶姆特蘭的基督教化
[編輯]在耶姆特蘭中部的弗勒瑟島上,矗立著世界上位置最北的盧恩石刻。碑文記載,有一位名叫奧斯特馬茲(Austmaðr)的人將基督教傳播到了該地區。這一事件大約發生在公元1030至1050年間,即石碑立成的時間。關於奧斯特馬茲的身份,目前尚無確切結論。
挪威的基督教化
[編輯]
挪威歷史上首次有記載的基督教傳教活動,由哈康一世發起。哈康一世自幼在英格蘭接受基督教教育。成為統治者後,他試圖在挪威推廣這一信仰。然而,由於民間反對激烈,其努力收效甚微。其繼位者灰袍哈拉爾亦為基督徒,但他主要因摧毀異教神廟而聞名,這一行為在當時並未提高基督教的民眾接受度。
在挪威西南部地區,由於與不列顛群島聯繫緊密,部分地方領主在這一時期已皈依基督教,甚至可能早於丹麥國王藍牙哈拉爾的受洗[1]。總體而言,挪威的基督教化進程主要受英格蘭影響,來自德意志地區的影響則相對較小[31]。
灰袍哈拉爾之後,異教徒哈康·西居爾松執政(約971年~995年)。哈康復興異教的立場十分鮮明,他重建了前任國王所摧毀的神廟。當時,藍牙哈拉爾曾試圖強迫他改信基督教,但遭到拒絕。哈康不僅不再效忠丹麥,還在後來986年的希約隆加瓦格戰役中擊退丹麥軍隊的入侵。
995年,奧拉夫一世即位。他生於960年前後,青年時期曾多次參與維京遠征。986年,他在英格蘭西南的錫利群島遇到一位基督徒先知。先知預言道[82][頁碼請求][83]:
| “ | 你將成為偉大的國王,成就非凡功業。你將引領眾人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禮,這將惠及你自身,也造福他人。為了讓你相信我的話,記住這個預言:當你返回船隊時,會遭遇背叛與敵對勢力。你會在戰鬥中受傷,自覺時日無多,並被人用盾牌抬上船。然而你將在七日之內康復,隨後便會受洗。 | ” |
奧拉夫回到船上後,果然被一群叛變分子襲擊致傷。受此事影響,他在痊癒後就接受了洗禮。此後,他長期在英格蘭與愛爾蘭居住,不再劫掠基督教城鎮。995年,奧拉夫趁挪威局勢動盪之際回國。當時哈康正面對叛亂。奧拉夫成功說服叛軍擁立自己為王。哈康在逃亡過程中被其奴僕殺害。
奧拉夫一世不惜採用強制手段,將基督教全國化當作主要施政目標。通過摧毀異教神廟、拷打甚至處決異教徒,奧拉夫至少在形式上實現了挪威部分地區的基督教化。《王室薩迦》還將法羅群島、奧克尼群島、冰島和格陵蘭島的基督教化也歸功於奧拉夫。不過,上述地區在奧拉夫發起全面傳教活動之前,就已有基督教扎根。《王室薩迦》又將奧拉夫描述成挪威首位基督徒,另一部薩迦《世界之圓》也有類似記載。然而事實上,奧拉夫面對的異教勢力主要集中於特倫德拉格及內陸地區;而在挪威西南部,基督教早在此前數十年就已逐漸傳播開來。因此,奧拉夫在西南地區的傳教工作,更可能是在鞏固當地的基督教化。而他對特倫德拉格地區的征服及強制改宗,則更顯著地推進了全國範圍內的基督教化進程[84]。
公元1000年,奧拉夫在斯沃爾德海戰中戰敗後,挪威一度在拉德侯爵的統治下出現短暫的異教復興。直至奧拉夫二世掌權後,異教再次遭到打壓,基督教的地位得以鞏固。
冰島的基督教化
[編輯]

1000年,冰島議會正式決定,全國皈依基督教。這一歷史事件在冰島語中被稱為「Kristnitaka」,字面意義為「採納基督教」。然而,該決定的附帶條款同時允許國民在私人場合繼續信奉原有宗教。因此,1000年傳統上被視作冰島改宗基督教的年份。關於這一轉變最重要的史料來源,是由阿里·索爾吉爾松撰寫的《冰島人之書》,此外還有若干家族薩迦、以及早期主教與神職人員的文獻記載。阿里的敘述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儘管他出生於冰島改宗67年後,但與此事的幾位親歷者有親戚關係,因而可以借鑑當時的口述傳統還原事件經過[85]。
當第一批移民於9至10世紀定居冰島時,他們內部可能已有部分基督徒,其中不少人來自基督教盛行的不列顛群島,在來冰島之前就已受洗歸信。然而大多數定居冰島的移民仍為信奉北歐舊教的教徒,有組織的基督教很快在當地消亡。大約公元980年起,陸續有多位傳教士造訪冰島,第一位可能是冰島人索瓦爾德·康拉德松(Þorvaldr Konráðsson inn víðförli)。他曾在海外旅行途中皈依基督教,並帶回一位德籍主教(該主教身份資料不詳)。他們嘗試向更多冰島人傳教,但收效甚微。托瓦爾德遭到當地人嘲諷。在一場造成兩人死亡的衝突後,他與隨行主教被迫逃亡[86]。
當奧拉夫一世在挪威登基後,冰島的基督教化進程明顯加快。雖然冰島名義上是自由邦,但挪威國王依然宣稱擁有該島的宗主權。奧拉夫國王派出一位冰島本地的基督徒斯特夫尼·索爾吉爾松(Stefnir Þórgilsson)前去傳教。然而斯特夫尼的手段過於激進。他摧毀神廟和舊教神像,激起了民怨,最終被宣判為「不法之徒」。斯特夫尼失敗後,奧拉夫改派一位名為桑布蘭德的神父。唐布蘭德曾在挪威與法羅群島進行過傳教工作,經驗豐富。他約於997至999年間在冰島傳教,但也僅取得了部分成功。他雖然成功說服幾位酋長改信基督教,但在傳教過程中也殺死了兩三人。唐布蘭德隨後不得不返回挪威,向國王報告他的失敗。奧拉夫隨即採取更為激進的策略:他禁止冰島船隻進入挪威港口,切斷了冰島最重要的貿易聯繫,同時劫持挪威境內的冰島人作為人質——其中不少是冰島權貴的子嗣。奧拉夫威脅稱,若冰島不改宗,便將這些人處決[87]。

冰島聯邦的外交基本取決於與挪威的關係,因此冰島的基督教化問題很快上升到國家層面。冰島境內已經改信的基督徒開始利用奧拉夫的壓力推動全國改宗,國家因此分裂為針鋒相對的兩大派系,一度瀕臨內戰的邊緣[88]。這一衝突局勢在1000年(或999年)夏季的冰島議會上達到了頂峰,支持舊教與基督教的雙方幾乎要爆發武裝衝突。幸而有人居中調停,使得爭議得以在庭中解決。議會發言人索爾蓋爾·索爾克爾松是雙方公認的調解人。他本人是洛薩瓦滕地區的舊教祭司,性格溫和、持中,因而得到雙方的認可。
索爾蓋爾擔負著決定國家宗教取向的重任。雙方達成協議後,他裹著毛毯,沉思冥想了整整一晝夜。這一行為可能是基於某種占卜儀式[84]。翌日,索爾蓋爾宣布冰島將改奉基督教,前提是保留部分舊法:
- 允許在特定情況下遺棄嬰兒;
- 允許食用馬肉;
- 舊教儀式可在私人場合秘密舉行。
索爾蓋爾隨後親自將自己供奉的神像投入一處瀑布,此地隨後被稱為「眾神瀑布」[89]。此後,舊教信仰被逐出公共領域,不再具有維繫社會秩序與身份認同的功能,因而逐漸消亡[9]。
總體而言,冰島的基督教化是和平完成的。儘管改宗過程存在妥協,保留了部分舊教傳統,教會仍然予以接受,因為這種妥協在各地基督教化初期並不罕見。待到基督教在冰島站穩腳跟後,索爾蓋爾保留舊法的條款最終被悉數廢止[90]。
值得注意的是,有證據表明,早在維京時代之前,冰島就已有基督徒存在。根據史料記載,在挪威人定居冰島之前,島上曾居住著一批來自愛爾蘭的帕帕。不過,有關他們的物證和遺蹟都已消失殆盡,無法確切考證他們的存在情況[91]。
法羅群島的基督教化
[編輯]
來源:Sigga Óskarsdóttir
公元999年,奧拉夫一世派遣西格蒙杜爾前往法羅群島,命令他協同幾位神職人員,讓法羅人皈依基督教。他們的目標是使島民接受洗禮,成為「善良的基督徒」。當時,法羅群島的酋長是特龍杜爾。西格蒙杜爾率領三十名隨從,突襲住在格塔的特龍杜爾,武力威脅逼他改宗。於是,特龍杜爾與其他居民在議會聚面,但他們斷然拒絕信仰「白色基督」,認為基督教不過是西格蒙杜爾用以奪取法羅群島控制權的藉口。在會議上,憤怒的人群幾乎將西格蒙杜爾置於死地。此次挫敗後,西格蒙杜爾改變策略。他於夜間率眾潛航至戈塔,進入特龍杜爾的農莊,把他拖下床。特龍杜爾面臨兩個選擇:要麼懺悔後改宗基督教,要麼被斬首。迫不得已,特龍杜爾選擇了前者。西格蒙杜爾隨後命令法羅群島居民改信基督教。然而,近年來的考古研究證明,基督教早在西格蒙杜爾發動所謂「再基督教化」之前就已經傳入法羅群島。包括凱爾特式墓碑在內的多項遺蹟表明,西格蒙杜爾的行為實則是將島上原有的凱爾特基督教強行轉變為與挪威王權一致的天主教[92]。
格陵蘭島的基督教化
[編輯]
據《紅鬍子埃里克薩迦》記載,萊夫·埃里克松曾拜訪時任挪威國王的奧拉夫一世。當萊夫準備返程格陵蘭時,奧拉夫囑託他在當地傳播基督教。返航途中,萊夫曾迷失方向,在一片「未知之地」短暫滯留。回到格陵蘭後,萊夫遵照諾言,於1000年開始傳教。他的母親西約德希爾德率先皈依,又出資興建了一座教堂[93]。大約一百年後,格陵蘭的農民向挪威國王西居爾一世提請設立主教區。國王應允,並任命挪威神職人員阿納德(Arnald)為主教,駐地在加達農莊[94]。該農莊已被確認與今日伊加利庫牧羊村落(位於圖努利亞菲克峽灣上游東岸)的許多遺址相符。1924年在伊加利庫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一座主教墓葬,證實了該農莊即為主教駐地。這座墓葬是目前唯一能證明格陵蘭島曾有主教居住的考古證據。經碳-14測定,該墓葬年代約在13世紀末[94]。
芬蘭的基督教化
[編輯]
在文獻記載中,芬蘭直至13世紀依然信奉舊教,與外界孤立。然而考古資料表明,芬蘭與瑞典中部地區及哥特蘭島關係密切[95]。11世紀早期,芬蘭及瑞典相鄰地區的喪葬習俗明顯改變,說明基督教已經開始在這些地區扎根。因此,芬蘭西部地區的基督教化,早在瑞典十字軍東征之前一個世紀就已開始,甚至要早於基督教在烏普薩拉扎根之時,而芬蘭的其他區域則可能較晚才接受基督教[96]。傳說中12世紀埃里克九世十字軍東征,實則是針對那些早已皈依基督教的地區。儘管此役廣為流傳,其真實性依舊存疑[97]。隨著12世紀瑞典人在芬蘭的滲透勢力逐漸壯大,尤其是13世紀比爾耶爾伯爵所領導的芬蘭十字軍東征,當地基督教進一步鞏固。
值得注意的是,芬蘭語中有大量的基督教基本術語源自斯拉夫語族,這表明芬蘭的基督教化很可能受到了東方的影響,這一現象也可同早期瑞典基督教印證[41]。
薩米人的基督教化
[編輯]
薩米人起源於俄羅斯東北部,後來擴散至挪威、瑞典、芬蘭等多個國家,其歷史可追溯到一萬年前[98]。據估計,薩米人的基督教化始於13世紀。至18世紀初,新的傳教運動興起,主要目標是使薩米人由天主教改宗新教[99]。
據史料記載,瑞典傳教士佩爾·霍格斯特倫曾在18世紀40年代描述過薩米人的信仰情況。此外,18世紀上半葉,教會專門開辦了面向薩米人的傳教學校,意圖推進其基督化進程[100]。
北歐其他地區的基督化
[編輯]
從9世紀中期至13世紀,赫布里底群島、曼島以及都柏林曾處於北歐統治之下。然而,當地居民以蓋爾人為主,且在挪威人到來之前就已信奉基督教。例如,相傳曼島早在5世紀便由愛爾蘭傳教士毛霍爾德完成了基督教化。1130年代,曼島迎來了首位主教,但他後來放棄職務,轉行成為海盜。相比之下,奧克尼群島、設得蘭群島與法羅群島的北歐人比例更高,這些地區直到10世紀末仍以信仰舊教為主。相傳,奧克尼群島於995年由奧拉夫一世完成基督教化。當時,奧拉夫自愛爾蘭返回挪威途中經過奧克尼群島,召見了當地的西居爾伯爵,強命其改宗。西居爾拒絕後,奧拉夫以殺害西居爾之子赫維爾普為要挾,迫使其接受基督教。11世紀初,設得蘭群島任命了首位主教。設得蘭與法羅群島皈依基督教,大致與奧克尼群島的改宗同時[101]。
參見
[編輯]注釋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引用
[編輯]- ^ 1.0 1.1 1.2 1.3 1.4 Sawyer (1993), side 101.
- ^ Schwarz Lausten (1994), side 12.
- ^ McGuire (2008), side 92.
- ^ Lind, John H. Tissø - Kiev - Konstantinopel: Danske netværk i øst?. Lyngstrøm, Henriette; Sonne, Lasse C.A. (編). Vikingetidens aristokratiske miljøer. København: academia.edu. 2014 [9 June 20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13).
- ^ 5.0 5.1 5.2 5.3 5.4 McGuire (2008)
- ^ 6.0 6.1 Steinsland (2005), side 422.
- ^ 7.0 7.1 Anders Winroth. The Conversion of Scandinavia.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 ^ 8.0 8.1 8.2 8.3 Warmind (1994), side 163.
- ^ 9.0 9.1 9.2 9.3 9.4 Warmind (1994), side 173.
- ^ Meulengracht Sørensen (2006), side 128.
- ^ Schwarz Lautsen (2008), side 12.
- ^ 12.0 12.1 Christianity on the move: the role of the Varangians in Rus and Scandinavia, in Fedir Androshchuk, Jonathan Shepard and Monica White (eds), Byzantium and the Viking World (Act.... [2025-05-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1-04).
- ^ McGrath (2006), side 320.
- ^ Bagge (2000), side 13.
- ^ 15.0 15.1 Schön 2004, side 170.
- ^ Bøgh (1999), side 66.
- ^ Ingeman (1999), side 101.
- ^ Kristus hjertingkirke.dk Hentet den 5. juni 2013.. [4. juni 2013]. (原始內容存檔於19. september 2015).
- ^ 19.0 19.1 19.2 19.3 19.4 Sawyer (1993), side 100.
- ^ 20.0 20.1 20.2 Olsen (1992), side 152.
- ^ Warmind (1994), side 169-170.
- ^ 22.0 22.1 Warmind (1994), side 170.
- ^ Sawyer (1993), side 102.
- ^ Historikere gør op med Harald Blåtands kristning af Danmark | Kristeligt Dagblad. [2025-05-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8-05).
- ^ Ellis Davidson (1964), side 223.
- ^ 26.0 26.1 Bagge (2000), side 28.
- ^ 27.0 27.1 Sawyer (1993), side 107.
- ^ Sawyer (1993), side 108.
- ^ 29.0 29.1 Warmind (1994), side 165.
- ^ 30.0 30.1 30.2 30.3 Ellis Davidson (1964), side 220.
- ^ 31.0 31.1 Olsen (1992), side 155.
- ^ Olsen (1992), side 156.
- ^ Hamilton (1986), side 17.
- ^ 34.0 34.1 Olsen (1992), side 158.
- ^ 35.0 35.1 Warmind (1994), side 178.
- ^ Mundal (2000), side 42-43.
- ^ 37.0 37.1 Schwarz Lausten (1994), side 16.
- ^ Schwarz Lausten (1994), side 26.
- ^ Olsen (1992), side 154.
- ^ Sawyer (1992), side 60.
- ^ 41.0 41.1 Lehtosalo-Hilander (2000), side 37.
- ^ Capelle (1993), side 177.
- ^ Warmind (1994), side 168.
- ^ 44.0 44.1 44.2 44.3 Sawyer (1993), side 105.
- ^ Ellis Davidson (1964), side 221.
- ^ Warmind (1994), side 176.
- ^ 47.0 47.1 47.2 Lund et.al. (1994), side 144.
- ^ Sawyer (1993), side 106.
- ^ Warmind (1994), side 167.
- ^ Schwarz Lausten (1994), side 33.
- ^ Warmind (1994), side 169.
- ^ Ellis Davidson (1964), side 222.
- ^ Lund et.al. (1994), side 143.
- ^ Ellis Davidson (1964), side 219.
- ^ Sawyer (1993), side 104.
- ^ Sawyer (1993), side 229.
- ^ Schön (2004), side 172.
- ^ Schön (2004), side 173.
- ^ Capelle (2005), side 169.
- ^ Capelle (2005), side 168.
- ^ Capelle (2005), side 177.
- ^ 62.0 62.1 Capelle (2005), side 167.
- ^ Schwarz Lautsen (1994), side 35.
- ^ Capelle (2005), side 171.
- ^ Capelle (2005), side 176.
- ^ Schwarz Lautsen (1994), side 34.
- ^ Capelle (2005), side 174.
- ^ Sawyer (1993), side 60.
- ^ Schwarz Lautsen (1994), side 17.
- ^ Olsen (1992), side 153.
- ^ Warmind (1994), side 171.
- ^ Hvitfeldt, Arild. Danmarks Riges Krønike
- ^ 73.0 73.1 "St Willibrord" Catholic Encyclopedia, (1913).
- ^ Robinson (1917).
- ^ 75.0 75.1 "Ancient See of Hamburg". Catholic Encyclopedia. (1913).
- ^ "Danmarks Ældste Domkirke" Kristelig Dagblad 25. juli 2007. Traditionen stammer fra Ribe bispekrønike: "Så blev den frisiske præst Leofdan (Lifdag) den første bisp i Ribe, hvem den vantro hob forfulgte under hans prædiken og dræbte med spyd, da han satte over en å. Men af de troende blev han begravet på den hellige Jomfrus kirkegård og over hans grav blev der rejst en opbygning. Senere blev han flyttet inden for kirkens mure i den nordlige del af den over for koret og i lang tid strålede den ved jærtegn hædret med de dengang tilbørlige hædersbevisninger". Overleveringen er afvist af Harald Andersen under henvisning til, at den ikke omtales af Adam af Bremen og til, at Leofdag ikke blev helgenkåret, se H.A.: "Martyr?" (Skalk 2004 nr. 1, side 18 ff.)
- ^ 77.0 77.1 Kaufhold (2001), side 86.
- ^ Kaufhold (2001), side 85.
- ^ Lagerquist (1997), side 44.
- ^ Larsson (2002), side 160.
- ^ Larsson (2002), side 161.
- ^ Rafn (1832).
- ^ Heimskringla. Hjemmeside der har oversat bogen 'Færeyínga saga' fra islandsk til dansk og norsk. Hentet den 7. juni 2013.
- ^ 84.0 84.1 Sawyer (1993), side 103.
- ^ Grønlie (2006), side xvi - xvii.
- ^ Grønlie (2006), side 38.
- ^ Grønlie (2006), side 47.
- ^ Grønlie (2006), side 49-50.
- ^ Christianity, hjemmeside om det islandske parlament.
- ^ Jones (1986), side 149-51.
- ^ Sigurdsson (2008), side 43.
- ^ Steffen Stummann Hansen : Early church sites in the Faroe Islands – a survey and a discussion. I: Acta Archaeologica vol. 82, 2011, side 55-80.
- ^ Arneborg (2002), side 10.
- ^ 94.0 94.1 Arneborg (2002), side 14.
- ^ Lehtosalo-Hilander (2000), side 32.
- ^ Lehtosalo-Hilander (2000), side 35.
- ^ Lethosalo-Hilander (2000), side 36.
- ^ Dixon (1994), side 148.
- ^ Mundal (2012), side 341 ff.
- ^ Axelson (2011), side 123.
- ^ Rafn (1832), kapitel 38.
來源
[編輯]- Arneborg, Jette m.fl. (2002) Kristningen af Norden, Nr. 21. Center for Middelalderstudier, Syddansk Universitet, Odense. ISSN 1601-1899 (丹麥文)
- Axelson, Per og Peter Sköld (ed.) (2011) Indigenous Peoples and Demography: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Identity and statistics. Berghahn Books. ISBN 0-85745-000-X (英文)
- Bagge, Sverre (2000); Kristendom og kongemakt, i Niels Lund (red.), Viking og hvidekrist. Norden og Europa in den sene vikingetid og tidligste middelalder, København ISBN 87-7876-189-1 (挪威文)
- Bøgh, Anders (1999); Kongen og hans magt, i; Middelalderens Danmark; kultur og samfund fra trosskifte til reformationen. ISBN 87-12-03863-6
- Bæksted, Anders (1996). Nordiske guder og helte , København. ISBN 87-567-5707-7
- Bavnbæk, Birthe (2012). Det tilslørede køn - den som bærer vandet. Kvinderne og apostelrollen. København. Forlag bbart. ISBN 978-87-994045-2-0
- Capelle, Torsten (2005); Hedensk og kristen tro, en anspændt sameksistens. i T. Capelle et.a.l (red.); Ragnarok, Odins verden. Silkeborg.
- Dixon, John E. og Robert P. Scheurell (ed.) (1994) Social Welfare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Routledge. ISBN 0-415-05564-4 (英文)
- Ellis Davidson, Hilda R. (1964); Gods and Myths of Northern Europe, London (英文)
- Grønlie, Sian (2006). The Book of the Islanders. The Story of the Conversion, Viking Society for Northern Research,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Tekst i pdf-forma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英文)
- Hamilton, Bernard (1986); Religion in the Medieval West, London ISBN 0-7131-6461-1 (英文)
- Hansen, Steffen Stummann Hansen (2011) Early church sites in the Faroe Islands – a survey and a discussion. I: Acta Archaeologica vol. 82. side 55-80. (英文)
- Ingesman, Per (1999); Kirken i samfundet, i; Middelalderens Danmark; kultur og samfund fra trosskiftet til reformationen. ISBN 87-12-03863-6
- Jones, Gwyn (1986), The North Atlantic Saga: Being the Norse Voyages of Discovery and Settlement to Iceland, Greenland, and North America, Oxford U. Press. (英文)
- Kaufhold, Martin (2001), Europas Norden im Mittelalter,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德文)
- Lagerquist, Lars O. (1997). Sveriges Regenter, från forntid till nutid. Norstedts, Stockholm. ISBN 91-1-963882-5 (瑞典文)
- Larsson, M. G. (2002). Götarnas riken. Upptäcksfärder till Sveriges enande. Atlantis, Stockholm. ISBN 91-7486-641-9. (瑞典文)
- Lehtosalo-Hilander, Pirkko Liisa (2000); Finnernes kristning, i N. Lund (red.) Viking og Hvidekrist; Norden og Europa i den sene vikingetid og tidligste middelalder, København ISBN 87-7876-189-1 (挪威文)
- Lund et.al. (1994): Erik Lund, Mogens Pihl og Johannes Sløk; De europæiske idéers historie. ISBN 87-00-54816-2
- McGuire, Brian Patrick (2008)¸ Da himmelen kom nærmere : fortællinger om Danmarks kristning 700-1300, Frederiksberg. ISBN 978-87-91191-47-3
- McGrath , Alister E. (2006). Christianity: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ISBN 1-4051-0901-7 (英文)
- Meulengracht Sørensen, Preben (2006); Kapitler af Nordens litteratur i oldtid og middelalder. ISBN 87-7934-219-1
- Mundal, Else (2000); Korleis påverka kristninga og kyrkja kjønnsrollemønstra?, i; i N. Lund (red.) Viking og Hvidekrist; Norden og Europa i den sene vikingetid og tidligste middelalder, København. ISBN 87-7876-189-1
- Mundal, Else (2012); Fjǫld veit hon fræða, Novus forlag, Oslo. Indeholder blandt andet artiklerne: «Kong Håkon Magnussons rettarbot for Hålogaland i 1313 og andre kjelder til kristninga av samane i mellomalderen» og «Korleis påverka kristninga og kyrkja kjønnsrollemønsteret?». (挪威文)
- Olsen, Olaf (1992); Kristendommen og kirkerne, i Roesdahl (red.) Viking og Hvidekrist; Norden og Europa 800-1200. , København. ISBN 87-7303-556-4
- Rafn, Carl Christian (1832); Færeyínga Saga. København. Bogtrykker Jens Hostrup Schultz. Link til Rafns oversættelse der findes på sprogene (丹麥文)(挪威文)(冰島語)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冰島語)
- Robinson, Charles Henry (1917); The Conversion of Europe. Londo mans, Green and Co. (英文)
- Sawyer, Birgit & Peter (1993); Medieval Scandinavia, Minnesota ISBN 0-8166-1738-4 (英文)
- Schön, Ebbe. (2004). Asa-Tors hammare, Gudar och jättar i tro och tradition. Fält & Hässler, Värnamo. ISBN 91-89660-41-2 (瑞典文)
- Schwarz Lausten, Martin (1994); Danmarks kirkehistorie. ISBN 87-00-12644-6
- Schwarz Lautsen, Martin (2008); Kirkens historie i Danmark. 2. udgave. ISBN 87-90645-02-2
- Sigurdsson, Jon Vidar (2008); Det norrøne samfunnet, Forlaget Pax, Oslo. ISBN 978-82-530-3147-7 (挪威文)
- Steinsland, Gro (2005); Norrøn religion. ISBN 82-530-2607-2
- Warmind, Morten (1994); Religionsmøde og trosskifte i N. Lund (red.) Norden og Europa i vikingetid og tidlig middelalder, København. ISBN 87-7289-240-4
延伸閱讀
[編輯]- Kristningen af Norden. Center for Middelalderstudier Syddansk Universitet. (pdf)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2-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