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離症
| 解離症 | |
|---|---|
| 症狀 | 意識、記憶、身份、情緒、感知、身體知覺、運動控制或行為的整合受損 |
| 併發症 | 情緒障礙、功能障礙、共病精神疾病 |
| 起病年齡 | 多於童年或青少年期起病 |
| 病程 | 可為短暫或長期 |
| 類型 | 解離性身份識別障礙、解離性健忘症、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等 |
| 病因 | 嚴重創傷、慢性壓力、藥物影響等 |
| 風險因素 | 童年虐待、慢性創傷、情緒忽視等 |
| 診斷方法 | 臨床評估(DSM-5或ICD-11標準) |
| 鑑別診斷 | 癲癇、神經認知障礙、藥物誘發狀態等 |
| 預防 | 無特定預防措施 |
| 治療 | 心理治療(如創傷治療) |
| 藥物 | 無特效藥物,可能輔助用抗憂鬱劑或抗焦慮藥 |
| 預後 | 多數病例可通過長期治療緩解 |
| 盛行率 | 依亞型不同而異 |
| 死亡數 | 極少直接致死,若伴自傷或自殺風險可能危及生命 |
| 分類和外部資源 | |
| 醫學專科 | 精神病學 |
| ICD-11 | 6B6 |
| ICD-10 | F44 |
| ICD-9-CM | 300.12-300.14 |
| MeSH | D004213 |
解離症[3](dissociative disorders,DDs,中國大陸稱分離性障礙[1][2])是一組心理障礙,其特徵為「意識、記憶、身份、情緒、感知、身體知覺、運動控制及行為等方面的整合發生重大中斷或破碎」。此類障礙通常涉及非自主性的解離反應,是一種無意識的心理防禦機制,目的是幫助個體在面對創傷性壓力時將痛苦經驗從主觀意識中分離。
某些解離症由嚴重的心理創傷引發,而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則可能由較輕的壓力、精神活性物質影響,或無明顯誘因的情況下發作。[4]
根據美國精神病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以下是主要的解離症類型:[5]
- 解離性身份識別障礙(DID,原稱「多重人格障礙」):表現為兩個或以上不同人格狀態之間的交替,且這些人格之間常存在記憶缺失。在嚴重個案中,主要人格對其他人格狀態毫無察覺,而某些「副人格」則可能知曉所有人格狀態。[6]
- 解離性健忘症(原稱「心因性健忘症」):個體無法回憶情景記憶,通常與創傷性或高壓事件相關,是最常見的解離性障礙之一。發作可突然或逐漸發生,持續時間從數分鐘到數年不等。[7][8] 原先獨立分類的解離性遊走現已作為「解離性健忘症」的特指類型(specifier),但許多遊走個案最終診斷為解離性身份識別障礙。[9]
- 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DpDr):個體出現對自我或外部環境的脫離感,主觀體驗為「不真實」,但同時意識到這是一種感覺而非現實。典型表現包括情感淡漠、「靈魂出竅」體驗、視覺模糊或失真、對熟悉事物的陌生感,甚至認不出鏡中的自己。還可能出現對飢餓、口渴等身體感覺的缺失。部分患者每日持續經歷上述症狀,也有人以間歇性發作形式呈現,每次持續1小時以上。
- 《DSM-IV》中的「未另作分類的解離性障礙」被拆分為:其他特定解離性障礙(OSDD)與未特定解離性障礙(USDD)。這兩個類別用於描述未完全符合其他標準的病態解離表現,包括尚無法明確分類或短暫性障礙等情況。[5] 其中,OSDD又細分多個子類型,OSDD-1屬於解離性身份識別障礙譜系,在國際疾病分類中被稱為「部分DID」。
在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版(ICD-11)中,解離性障礙包括:[10]
- 解離性神經症狀障礙(又稱「功能神經系統障礙」)
- 解離性健忘症
- 伴隨解離性遊走的解離性健忘症
- 恍惚障礙
- 附體現象恍惚障礙
- 完全型解離性身份識別障礙
- 部分型解離性身份識別障礙
- 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
原因與治療
[編輯]解離性障礙通常被視為一種應對心理創傷的防禦機制。患有此類障礙的人,往往在童年時期經歷過長期的身體虐待、性虐待或情緒虐待;也有少數患者是在一個極具威脅性或高度不可預測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然而,部分類型的解離性障礙也可能由成年後出現的創傷事件引發,如戰爭或親人去世,這些並不一定涉及虐待。
尤其是解離性身份識別障礙(DID),在治療時應避免賦予其超自然或神秘色彩。更科學的做法是將其視為其他心理疾病一樣加以臨床研究與治療。[11]
解離性身份識別障礙(DID)
[編輯]成因: DID的成因仍具爭議,主流觀點認為其多起源於6至9歲之前的持續性童年創傷。[12][13] 另有理論認為DID可能為治療過程、幻想傾向或社會誘發因素的「非故意產物」。[14]
治療: 長期心理治療可幫助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常見方法包括:
儘管上述藥物可用於緩解DID及其他解離性障礙的症狀,但目前尚無專門用於治療解離性障礙的特效藥物。[15]
解離性健忘症
[編輯]成因: 心理創傷是主要原因。雖然許多患者有童年虐待史,但這並非發病的必要條件。[16]
治療: 以心理諮詢或心理社會治療為主,主要通過與專業心理醫生交流處理與障礙相關的情緒與記憶。在某些情況下,硫噴妥鈉可用於協助恢復記憶。[17]
遺忘發作可能持續數分鐘至數年不等,若與創傷事件相關,則當個體脫離創傷環境後,記憶有可能逐漸恢復。
人格解體-現實解體障礙
[編輯]成因: 儘管與其他解離性障礙的關聯不如DID明顯,但研究表明,該障礙與童年創傷,尤其是情緒忽視或虐待,有一定關聯。此外,重大生活壓力事件,如親人突然去世,也可能誘發該障礙。[18]
治療: 治療方式與解離性健忘症相似。發作可能短至幾秒鐘,長則可持續多年。[17]
神經科學
[編輯]腦活動的差異
[編輯]解離性障礙患者在多種腦區的活動上與常人存在明顯差異,包括頂下小葉、前額葉皮質和邊緣系統等區域。[19]
與健康對照組相比,解離性障礙患者的前額葉活性通常更高,而邊緣系統的活動則呈抑制狀態。[19]這種「皮層—邊緣系統的抑制增強」被認為與典型的解離症狀(如人格解體和現實解體)密切相關,這些反應被視為應對極端威脅或創傷事件的心理應激機制。[20]
通過抑制邊緣系統中如杏仁核等結構,大腦可降低過度激發水平。在解離型創傷後壓力障礙中,既存在對情緒的過度控制(邊緣結構被抑制),也存在情緒的控制不足(中額前皮質過度激活)。其中,中額前皮質的活性增加常與非解離性症狀(如創傷重現、過度警覺)相關。[19]
腦結構體積的差異
[編輯]研究發現,解離性障礙患者在某些腦區(如海馬體與杏仁核)的皮質與皮下結構體積普遍減少。[21]
杏仁核體積減少被認為與解離狀態下的情緒反應減弱有關;而海馬體是學習與記憶的重要區域,其體積減少與DID和創傷後壓力障礙中的記憶障礙相關。[22]
腦部影像研究已證實海馬體積減少與DID和PTSD相關聯,這也進一步支持這些障礙的存在。同時,還有研究指出,海馬體積與童年創傷存在負相關性,後者被認為是解離症狀的潛在成因之一。[23][2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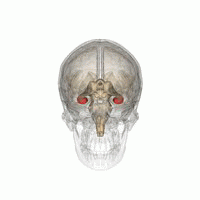

藥物治療
[編輯]目前尚無可「治癒」或「根治」解離性障礙的專用藥物,但可根據共病症狀使用抗焦慮藥或抗憂鬱藥進行輔助治療。[26]
診斷與流行病學
[編輯]解離性障礙的終生盛行率在一般人群中約為10%,在精神科住院患者中可高達46%。[27]
診斷通常依賴於結構化臨床訪談,如解離性障礙訪談量表(DDIS)和《DSM-IV解離性障礙結構化臨床訪談修訂版》(SCID-D-R),以及在訪談過程中的行為觀察。[27][28]
額外的信息,如解離經驗量表、其他問卷、基於表現的測驗、醫療或學業記錄,以及來自配偶、父母或朋友的反饋也有助於診斷。[28] 單次會面無法排除解離性障礙的可能,許多最終確診的患者此前從未獲得此診斷,部分原因是臨床醫生缺乏對解離症狀的識別訓練。[28]
針對兒童與青少年,也開發了相應的測評工具,如青少年解離經驗量表、青少年反應評估量表(REM-Y-71)、兒童主觀解離體驗訪談、兒童解離檢查表(CDC)、兒童行為量表(CBCL)中的解離子量表,以及創傷症狀量表中的解離部分。[29][30]
研究發現,解離性障礙在門診和低收入社區中也較為普遍。在一項研究中,貧困的市中心門診人群中,解離性障礙的盛行率達到了29%。[31]
解離性障礙與轉換障礙在分類、診斷與治療策略上長期存在爭議,其歷史背景可追溯至「歇斯底里」的概念。目前主流診斷體系,如DSM-IV與ICD-10,在分類方式上也有所不同。[32]
多數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在診斷解離性障礙時仍持謹慎態度,常見於患者在接受DID診斷之前,已被診斷為重度憂鬱疾患、焦慮症或創傷後壓力障礙。[33]
與自填量表相比,通過訪談方式進行的診斷對識別解離性障礙更有效。[31]
由於診斷障礙的複雜性,解離性障礙的實際流行率尚不完全清楚。障礙的誤解、對其症狀的不熟悉、甚至對其存在的質疑,都導致了較低的診斷率與治療率。[34]
數據顯示,僅有28%至48%的解離性障礙患者接受了心理健康相關治療。[35] 被誤診的患者往往面臨更高的住院率、頻繁的門急診就診以及更高的殘疾率。[35]
在司法環境中,診斷解離性障礙也存在挑戰,例如個體可能偽造症狀以逃避責任。研究顯示,青少年罪犯中報告健忘症的比例顯著較高,約1%聲稱對暴力犯罪完全失憶,19%表示部分失憶。[36] 也有案例顯示,患有解離性身份識別障礙的被告,在庭審中依據不同「人格」可能作出相互矛盾的證詞。[37][需要較佳來源]
全球範圍內,解離性障礙的盛行率尚不明確,這部分受限於不同文化對情緒和大腦功能的理解差異。[38]
兒童與青少年
[編輯]解離性障礙(DD)普遍被認為與不良童年經歷(如虐待與失落)有關,但在兒童和青少年中的症狀往往未被識別或被誤診。[30][39][40]
然而,一項中國西部的研究顯示,公眾對於兒童中存在的解離性障礙的認知有所提高。[41] 研究指出,解離性障礙與患者的心理、生理和社會文化環境之間存在複雜關係。[41] 該研究還指出,解離性障礙在西方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更為常見,儘管在中國臨床和非臨床人群中也有確診案例。[41]
識別兒童解離症狀具有挑戰性,其原因包括:兒童難以表達自身內在體驗;照護者可能忽略或掩蓋虐待/忽視行為;[30] 症狀可能表現為微妙且短暫;而且與解離相關的記憶、情緒或注意力障礙,常被誤判為其他疾病。[30]
英國Beacon House指出,兒童中的解離常是未被察覺的「生存機制」,尤其在遭受創傷的兒童中較常見。[42] Dr. Shoshanah Lyons 指出,許多創傷兒童在脫離危險後仍持續解離,而且他們往往意識不到自己處於解離狀態。[42]
除了開發適用於兒童與青少年的評估工具(見前文),研究者也致力於提升解離識別能力,並深入探討創傷導致的神經化學、功能性與結構性腦部異常。[39] 有學者主張,識別無序依附(DA)可作為判斷兒童是否存在解離障礙的線索之一。[40]
2008年,Rebecca Seligman 與 Laurence Kirmayer 指出,童年創傷與個體發展出解離能力之間存在顯著聯繫,且這些能力可能被長期用作應對壓力的機制。[43]
臨床專家與研究人員普遍認為,應使用發展心理學視角來理解解離性障礙的症狀與未來發展軌跡。[30][39] 換言之,解離症狀在不同年齡階段可能以不同方式表現,個體在不同成長階段的易感性亦有所差異。目前仍需進一步研究,探討解離症狀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表現機制與風險因素。[30][39] 此外,也需要研究年輕患者的康復是否具有長期穩定性。[44]
當前爭議與DSM-5
[編輯]關於解離性障礙的多個方面目前仍存在活躍的學術爭議。首先,圍繞解離性身份識別障礙(DID)的病因學仍有分歧。爭議焦點在於:DID是否源自童年創傷或無序依附,[39][45] 亦或是否具有生理機制,如自動觸發的高血壓、警覺性等反應,從而支持其作為跨物種的防禦機制存在。[46]
其次,學界也在探討「作為防禦機制的正常解離」與「病理性解離」之間是否存在質的差異。解離體驗的表現從日常經驗延伸至創傷後壓力障礙(PTSD)、急性應激障礙(ASD)及正式的解離性障礙診斷之間存在連續性。[30]
考慮到這種複雜性,DSM-5的工作小組曾考慮將解離性障礙劃入創傷及壓力相關障礙一章,[47] 最終仍將其單列章節,以強調其與創傷障礙的緊密關係。[48] DSM-5 還新增了PTSD的「解離亞型」。[48]
一篇2012年的綜述文章支持這樣一種觀點:當前或近期的創傷可能會改變個體對過去事件的感知,從而引發解離狀態。[49]
然而,認知科學的實驗研究不斷挑戰「解離」概念的有效性,其理論基礎仍大多依賴皮埃爾·雅內提出的「結構性解離」模型。[7][50]
即使「創傷/虐待」與「解離」之間的因果關係也受到質疑。有研究指出,這種關聯多出現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而在某些非西方文化中,解離可能被視為「正常心理能力」的一部分。[來源請求]
另一種模型則提出:解離現象與睡眠-覺醒周期的不穩定性有關,這種不穩定會導致記憶錯誤、認知失誤、注意力控制問題,以及難以區分幻想與現實。[51]
近年來部分心理學家與網絡社區倡導多意識體這一概念,認為DID等部分解離現象可理解為有多個意識或人格在同一身體內生活,這種狀態可能是病理性的,但是在許多情況下也可以是健康的,甚至是積極的,是神經多樣性的體現。一些人主動追求類似狀態,如圖帕(tulpa)實踐。
圍繞DD的爭議也與西方與非西方文化差異密切相關。DID最初被認為僅存在於西方,直到跨文化研究證實其在全球範圍內皆有出現。[46] 然而,人類學界對西方文化中的解離現象研究相對較少,對「附體現象」在非西方社會的研究亦存在片面性。[來源請求]
儘管西方與非西方社會對解離現象的理解與分類不同,但兩者仍體現了解離性障礙的某些普遍特徵。例如,非西方社會中的薩滿教儀式常涉及解離狀態,但類似現象也存在於西方某些基督教教派(如「聖靈附體」)中。[來源請求]
參見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分离性障碍. 術語在線.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簡體中文)
- ^ 陸林,李濤.精神病学 [M]. 9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24-11. 978-7-117-36773-8.
- ^ dissociative disorder. 樂詞網. 國家教育研究院 (中文(臺灣)).
- ^ Simeon, D; Abugel, J. 感觉不真实:人格解体障碍与自我的丧失. 紐約: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6: 17. ISBN 0195170229.
- ^ 5.0 5.1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DSM-5. 5th. Arlington, VA: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291–307. ISBN 9780890425541.
- ^ Schacter, D. L., Gilbert, D. T., & Wegner, D.M. (2011). Psychology: Second Edition, pp. 572–573. New York, NY: Worth.
- ^ 7.0 7.1 Maldonado, R.J.; Spiegel, D. 解离性障碍. 美国精神病学出版审查指南:精神病学 第七版.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2019. ISBN 978-1-61537-150-1.
- ^ First, M. B., 等主編. 《精神病學》第四版. 2015. p1187. ISBN 978-1-118-84547-9
- ^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DSM-5. 5th. Arlington, VA: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812. ISBN 9780890425541.
- ^ ICD-11 - 死亡与发病统计. icd.who.int. [2020-09-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01).
- ^ Deeley, P. Q. Social, Cognitive, and Neural Constraints on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Implications for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Philosophy, Psychiatry, & Psychology. 2003, 10 (2): 161–167. doi:10.1353/ppp.2003.0095.
- ^ Spigel, David; et al. Dissociative disorders in DSM5DMS. [2024-0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17).
- ^ Salter, Micahel; Dorahy, Martin; Middleton, Warwick.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exists and is the result of childhood trauma. The Conversation. 2017-10-04 [2024-0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12).
- ^ Vissia, E. M.; Giesen, M. E.; Chalavi, S.; Nijenhuis, E. R. S.; Draijer, N.; Brand, B. L.; Reinders, A. A. T. S. Is it Trauma- or Fantasy-based? Comparing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imulators, and controls.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16, 134 (2): 111–128. PMID 27225185. doi:10.1111/acps.12590.
- ^ 解离性障碍:治疗与药物. 梅奧診所. 2011-03-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10-22).
- ^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2013年,美國家精神病學會,第299頁,ISBN 9780890425541。
- ^ 17.0 17.1 Miller, John L. 解离性障碍. athealth.com. 2014-02-03 [2024-0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0-19).
- ^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2013年,美國家精神病學會,第304頁,ISBN 9780890425541。
- ^ 19.0 19.1 19.2 Spiegel, David; Lewis-Fernández, Roberto; Lanius, Ruth; Vermetten, Eric; Simeon, Daphne; Friedman, Matthew. Dissociative Disorders in DSM-5.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3-03-28, 9 (1): 299–326. doi:10.1146/annurev-clinpsy-050212-185531.
- ^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文本修订本(DSM-IV-TR). 美國精神病學會. 2009. ISBN 978-0-89042-024-9.
- ^ Lotfinia, Shahab; Soorgi, Zohre; Mertens, Yoki; Daniels, Judith. 解离体验精神疾病患者的脑部结构与功能变化: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系统综述.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20-09, 128: 5–15. doi:10.1016/j.jpsychires.2020.05.006.
- ^ Blihar, David; Delgado, Elliott; Buryak, Marina; Gonzalez, Michael; Waechter, Randall. 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神经解剖系统综述. European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2020-09, 4 (3): 100148. doi:10.1016/j.ejtd.2020.100148.
- ^ Reinders, A. A. T. S.; Chalavi, S.; Schlumpf, Y. R.; Vissia, E. M.; Nijenhuis, E. R. S.; Jäncke, L.; Veltman, D. J.; Ecker, C. 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中皮层形态异常的神经发育起源.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18-02, 137 (2): 157–170. doi:10.1111/acps.12839.
- ^ Chalavi, Sima; Vissia, Eline M.; Giesen, Mechteld E.; Nijenhuis, Ellert R.S.; Draijer, Nel; Cole, James H.; Dazzan, Paola; Pariante, Carmine M.; Madsen, Sarah K.; Rajagopalan, Priya; Thompson, Paul M.; Toga, Arthur W.; Veltman, Dick J.; Reinders, Antje A.T.S. 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海马体形态异常与童年创伤的相关性. Human Brain Mapping. 2015-05, 36 (5): 1692–1704. doi:10.1002/hbm.22730.
- ^ Blihar, David; Crisafio, Anthony; Delgado, Elliott; Buryak, Marina; Gonzalez, Michael; Waechter, Randall. 关于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患者海马体与杏仁核体积的元分析.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2021-05-27, 22 (3): 365–377. doi:10.1080/15299732.2020.1869650.
- ^ 什么是解离与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 Rethink Mental Illness. [2020-09-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0-22).
- ^ 27.0 27.1 Ross. 住院环境中解离性障碍的患病率、信度与效度.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2002, 3: 7–17. S2CID 144490486. doi:10.1300/J229v03n01_02.
- ^ 28.0 28.1 28.2 Bailey, Tyson D.; Boyer, Stacey M.; Brand, Bethany L. 解离性障碍. Diagnostic Interviewing. Springer. 2019. ISBN 978-1-4939-9127-3.
- ^ 儿童与青少年解离症状评估与治疗指南:国际解离研究学会 (PDF).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2004-10-04, 5 (3): 119–150 [2020-07-24]. S2CID 220430260. doi:10.1300/J229v05n03_09.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21-06-25).
-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Steiner, H.; Carrion, V.; Plattner, B.; Koopman, C. 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解离性症状:诊断与治疗.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002, 12 (2): 231–249. PMID 12725010. doi:10.1016/s1056-4993(02)00103-7.
- ^ 31.0 31.1 Foote, B. 精神科门诊患者中解离性障碍的患病率.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6, 163 (4): 623–629. PMID 16585436. doi:10.1176/ajp.2006.163.4.623.
- ^ Splitzer, C; Freyberger, H.J. 解离性障碍(转换障碍). Psychotherapeut. 2007.
- ^ Nolen-Hoeksema, S. (2014). 身體化症狀與解離性障礙. In 《異常心理學》(第6版,第164頁). 紐約:McGraw-Hill.
- ^ Coons, P. M. 解离性障碍:少被考虑且被低估的疾病.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1998, 21 (3): 637–648. PMID 9774801. doi:10.1016/S0193-953X(05)70028-9.
- ^ 35.0 35.1 Nester, M. S; Hawkins, S. L; Brand, B. L. 体验解离症状患者在获取与持续治疗上的障碍.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2022, 13 (1). PMC 8856065
 . PMID 35186217. doi:10.1080/20008198.2022.2031594.
. PMID 35186217. doi:10.1080/20008198.2022.2031594.
- ^ Evans, Ceri; Mezey, Gillian; Ehlers, Anke. 青少年罪犯对暴力犯罪的遗忘现象.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 Psychology. 2009, 20 (1): 85–106. doi:10.1080/14789940802234471.
- ^ Haley, J. 被告妻子就其多重人格作证. Bellingham Herald. 2003: B4.
- ^ Seligman, R; Brown, R. A. 人类学与文化神经科学交叉点的理论与方法.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10, 5 (2): 130–137. doi:10.1093/scan/nsp032.
- ^ 39.0 39.1 39.2 39.3 39.4 Diseth, T. 儿童与青少年的解离作为创伤反应:概念问题与神经生物学因素概述. Nordic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5, 59 (2): 79–91. PMID 16195104. doi:10.1080/08039480510022963.
- ^ 40.0 40.1 Waters, F. 识别学龄前儿童的解离症状. 國際解離研究學會通訊. 2005年7–8月, 23 (4): 1–4.
- ^ 41.0 41.1 41.2 Fang, Z. 中国西部儿童解离(转换)障碍的特征与结局:一项回顾性研究. BMC Psychiatry. 2021, 21 (1): 31. PMC 7802240
 . PMID 33435924. doi:10.1186/s12888-021-03045-0.
. PMID 33435924. doi:10.1186/s12888-021-03045-0.
- ^ 42.0 42.1 Lyons, S. 儿童与青少年中的解离现象. Beacon House 創傷心理治療中心. [2022-08-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29).
- ^ Seligman, R; Kirmayer, LJ. 解离体验与文化神经科学:叙事、隐喻与机制.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2008, 32 (1): 31–64. PMC 5156567
 . PMID 18213511. doi:10.1007/s11013-007-9077-8.
. PMID 18213511. doi:10.1007/s11013-007-9077-8.
- ^ Jans, Thomas; Schneck-Seif, Stefanie; Weigand, Tobias; Schneider, Wolfgang; Ellgring, Heiner; Wewetzer, Christoph; Warnke, Andreas. 儿童或青少年起病的解离性障碍:长期预后研究.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2008, 2 (1): 19. PMC 2517058
 . PMID 18651951. doi:10.1186/1753-2000-2-19.
. PMID 18651951. doi:10.1186/1753-2000-2-19.
- ^ Boysen, Guy A. 儿童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科学地位:已发表研究综述.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2011, 80 (6): 329–34. PMID 21829044. doi:10.1159/000323403.
- ^ 46.0 46.1 Lynn, C. D. 适应性与不良性解离:一种流行病学与人类学对比视角与解离模型扩展提案. Anthropology of Consciousness. 2005, 16 (2): 16–49. doi:10.1525/ac.2005.16.2.16.
- ^ Brand, Bethany L.; Lanius, Ruth; Vermetten, Eric; Loewenstein, Richard J.; Spiegel, David. 展望DSM-5:关于解离性障碍评估、治疗与神经生物研究的进展.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2012, 13 (1): 9–31. PMID 22211439. doi:10.1080/15299732.2011.620687.
- ^ 48.0 48.1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 第5版. 美國精神病學出版社. 2013: 528–556. ISBN 978-0-89042-557-2.
- ^ Stern DB. 跨时间的见证:从过去访问现在,从现在回顾过去.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2012年1月, 81 (1): 53–81. PMID 22423434. doi:10.1002/j.2167-4086.2012.tb00485.x.
- ^ Heim, Gerhard. Pierre Janet 对解离障碍病因、发病机制与治疗的看法. Craparo, Giuseppe (編). 重新发现皮埃尔·雅内 第1版. Routledge. 2019年4月3日: 178–199. ISBN 978-0-429-20187-5. doi:10.4324/9780429201875-14.
- ^ Lynn, SJ. 解离与解离性障碍:挑战传统观点.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21 (1): 48–53. doi:10.1177/0963721411429457.
